吉诺-多米尼克斯(Gino De Dominicis)的大型作品《Mozzarella in Carrozza》揭开了博洛尼亚 MAMbo 博物馆"Facile Ironia"展览的序幕,在这件作品之后,道路被分割成许多作品,这些作品往往会在装置艺术中迷失方向,不引人注目。Carrozza 的 Mozzarella》挑战了任何单一的解释,既有趣又令人迷失方向,是一个视觉笑话,在其看似简单的外表下,隐藏着对感知、语言和艺术本质的深层反思。时间与不朽,荒诞与形而上。马苏里拉奶酪被放在一辆古老的黑色马车的座位上,在强大和永恒的过去与物质的短暂和脆弱之间产生了一种概念上的短路。这是一个语言上的笑话,它以一种强烈而新颖的方式阐述了马塞尔-杜尚的现成品,然后像一个累赘的幽灵一样伴随着整个展览。
所有现代和当代艺术都是建立在概念偏差的基础上,对艺术作品的经典定义提出质疑,并必然具有 “讽刺 ”意味。正因如此,除了现当代艺术中充斥的苦涩的、概念性的反讽之外,展览还需要更正面、更直接的作品,以反映 2025 年我们在博物馆外强烈感受到的复杂而又跃动的现实。例如,加布里埃尔-皮科(Gabriele Picco)等艺术家以其讽刺性和梦幻般的绘画,以及朱利奥-阿尔维基尼(Giulio Alvigini)等能够将meme文化应用于艺术世界的艺术家,都没有参展。同时,里卡多-巴鲁齐 (Riccardo Baruzzi )和 费德里科-托西(Federico Tosi)(仅举两例)等艺术家似乎也是无端和被迫的选择。




在众多并不大的作品、小幅黑白照片、素描和小型干预作品中,我们错过了罗伯托-法索内的作品,尽管我们已经参观过两次展览,但我们还是喜欢伊塔洛-祖菲、毛里齐奥-梅尔库里(虽然作品有限)和弗朗切斯科-维佐利的作品。莫妮卡-邦维奇尼(Monica Bonvicini)和拉拉-法瓦莱托(Lara Favaretto)的作品过于小巧和简约,这一方面让人联想到博物馆近年来不得不面临的预算减半问题,另一方面也让人联想到讽刺意味并不那么强烈和突出的道路。例如,伊塔洛-祖菲(Italo Zuffi)微妙而概念化的反讽,让人觉得展览中应该有更多俏皮和正面的补充,因为他跟踪了拒绝他作为艺术家的画廊老板多日并拍摄了照片。
展览中专门讨论女性主义艺术中的反讽的部分并没有恢复这一运动的重要性: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有些作品无疑是重要的,但它们却显得软弱无力,与《2025》的复杂性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可比性。总的来说,为了理解和进入展出的作品,人们不得不阅读大量的、用小字写在彩色背景上的长篇说明。仔细想想,这就扼杀了讽刺的一个基本方面:即直接性。你会有一种类似于解释一个笑话的感觉。如果这样,我们显然就失去了正面性和直接性,而这正是激活作品讽刺性的根本所在。如果观众要阅读展览中的所有说明和许多作品中的文字,那将花费数小时,这将严重影响他或她的体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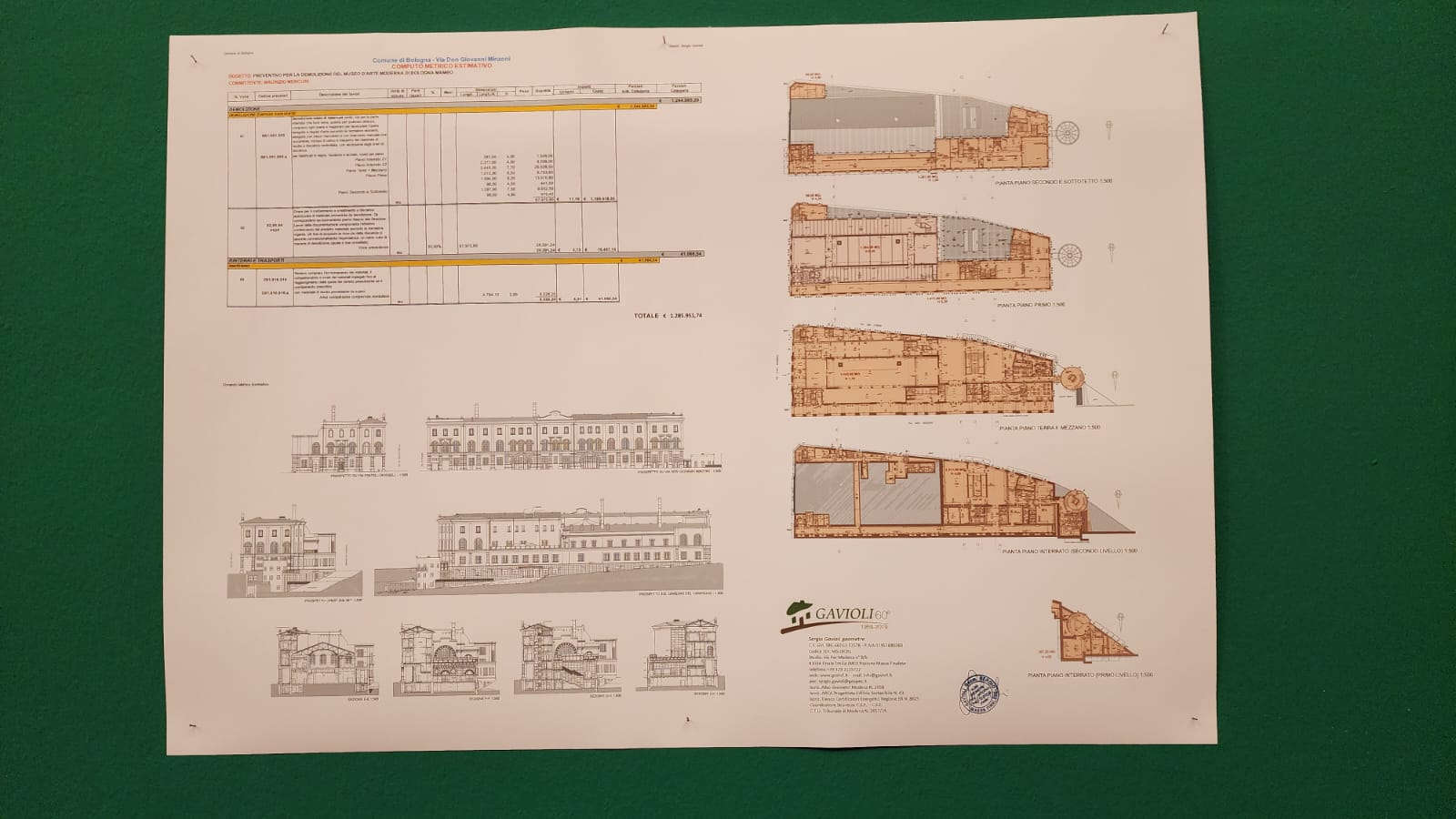



在 MAMbo,我们可以看到帕斯卡利、博埃蒂、阿卡迪、卡泰兰:他们都是伟大的艺术家,但在展览中,他们的作品也被墙壁的色彩和周围的众多作品所淹没。卡泰兰的鸽子,静止的和标本化的(《幽灵》),失去了咬合力,仍然有一种不满意的感觉,好像这些鸽子为了影响 2025 年(作品可追溯到 1997 年),至少应该是活的。
这次展览在历史意义上展示了解读 MAMbo 博物馆 50 周年的努力,但同时也再次显示了当代艺术和艺术体系在确定面对我们当下的方式、态度、愿景和态度方面的危机。我们的感觉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到今天出现的新一代艺术家和策展人,就像被搁浅在 20 世纪的浅滩、现成品和后现代之中,而引文无法成为有效解决当代问题的桥梁。
免责声明:本篇意大利语原文的中文翻译由自动工具生成。 我们承诺会对所有文章进行审核,但无法保证完全避免因软件造成的翻译误差。 您可以点击 ITA 按钮查看原文。如发现任何错误,请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