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现实主义的历史源远流长。这不仅是因为超现实主义经久不衰的影响力,更不是因为意大利国内外正在举行的百年庆典。从 2024 年 9 月 4 日至 2025 年 1 月 13 日蓬皮杜艺术中心欢迎参观者的时间顺序来看,我们谈论的是近半个世纪的研究:从 1924 年到 1969 年。由迪迪埃-奥廷格(Didier Ottinger)和玛丽-萨雷(Marie Sarré)策划的 "苏黎世主义"(Surréalisme)展览的时间顺序由这两个日期划定,这两个日期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们一劳永逸地肯定了苏黎世主义的悠久历史,而且,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苏黎世主义在地域上的普及性以及在最多样化的艺术流派中的丰富性。超现实主义传统上被列入 20 世纪早期的历史先锋派,它与其中一些先锋派--首先是未来主义或达达主义(它的后裔)--有一个共同的决定性问题,这个问题来自于在最不同方向上进行的单纯的美学和形式研究。超现实主义是一种世界观,一种以最难以预测的方式对待生活的方法,一种哲学。超现实主义从一开始就这样做了,在作为其创始行为的文件中:诗人兼潮流的第一位理论家安德烈-布勒东于 1924 年 10 月发表的宣言。
在 2024 年周年纪念之际,值得重读的是这份宣言的全文,它是图像、信仰、文学、 科学和魔法的大熔炉。因此,巴黎展览的参观者在参观的最初几分钟内就能接触到它绝非偶然。时间线是邀请参观者进入展览结构所依托的迷宫之前的最后一个安全立足点,参观者在穿过时间线之后,会立即穿过一个畸形的入口,看起来就像是游乐场里的鬼屋。毕竟,报纸上正是以这种方式讨论超现实主义展览的。1947 年 9 月 26 日,《战斗》在评论国际超现实主义博览会时写道:“这是一种没有任何语言名称的东西,它既像伦敦的杜莎博物馆,又像诺伊伊节,既像大篷车,又像格莱温博物馆。和 Grévin,类似于现已不复存在的月神公园的一个景点、Cabaret du Néant 和 de l’Enfer,类似于精神病院和卡里加利博士的实验室”。这些参考资料非常准确,让人重新感受到超现实主义对于 20 世纪中期的参观者来说是如何成为畸形幻象的源泉。在所有被唤起的地方中,Cabaret de l’Enfer(地狱夜总会)最引人注目,这是一家以地狱为主题的历史悠久的巴黎夜总会,罗伯特-杜瓦诺(Robert Doisneau)在 1952 年拍摄的一个著名镜头永恒地记录了它的入口,更早之前,欧仁-阿特金(Eugène Atget)至少在 1900 年和 1910 年左右拍摄过它的入口,之后它就消失在一家超市的外墙后面。因此,这一计划中的参照并非寓言式的,而是地形式的:展览的入口直接指向一个地狱般的地方,它代表了城市中众多超现实主义地点之一。对于 2024 年的周年纪念来说,这或许是最令人回味的地点之一。布勒东的工作室就在这栋建筑的四楼,从旁边的 Fontaine 路 42 号可以进入,如今这里还立着一块牌子,纪念 “1922 至 1966 年超现实主义运动中心”。正是在这里,1910 年代末开始了起草被认为是 20 世纪最重要著作之一的宣言的实验。事实上,该宣言是《可溶之水》一书的序言,旨在以白纸黑字的形式确定自动书写工艺的某些原则和目标,该工艺始于1919年,之后又于1930年和1942年发表了两篇宣言。
在展览入口处,该运动的法国代表在一条昏暗的走廊上欢迎参观者:André Breton, Suzanne Muzard, Salvador Dalí, René Magritte, Raymond Queneau, Jean Aurenche, Marie-Berte Aurenche, Max Ernst, Pierre and Jacques Prévert, Louis Aragon, Yves Tanguy, Paul ÉLuard, Jacques André Boiffard 和 Luis Buñuel 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拍摄的老式照相馆中出现,他们的举止粗鲁,有时甚至令人不安。简短的参观结束后,参观者来到布列塔尼手稿原稿陈列室。由于从 法国国家图书馆借出,该手稿首次完整展出。文件会说话。博物馆声学/音乐研究与协调研究所(IRCAM)的团队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一些历史录音和一名演员的参与,对论文进行了重构。当面孔、文字、情境和地图等图像在令人回味的沉浸式投影中流动时,超现实主义的坐标将指引作品之间的路径。
首先,布勒东通过电报对其进行了描述,在超现实主义研究局(Bureau de Recherche Surréalistes)领导的一份文件中,还可以阅读到展示下的印刷品。该组织也被称为 “超现实主义中心”(Centrale surréaliste),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将其描述为 “为新思想和新革命提供的罗马式庇护所”,在宣言发表前几天成立。其首批行动包括制作 16 张超现实主义纸片:黄色、绿色和粉红色的贴纸,效仿 1920 年特里斯坦-扎拉(Tristan Tzara)和保罗-艾吕雅(Paul Éluard)的达达主义行动,通过挑衅性和深奥的警句以及他们所说的定义,帮助在街头传播超现实主义革命:“SURRÉALISME, n. m. Automatisme psychique pur.m. Automatisme psychique pur par lequel on se propose d’exprimer, soit verbalment, soit par écrit, soit de toute autre manière, le fonctionnement réel de la pensée.Dictée de la pensée, en l’absence de tout contrôle exercé par la raison, en dehors de toute préoccupation esthétique ou morale”。超现实主义的语言或文字,无论采用何种方式,都是一种精神上的自动行为,旨在展现思想的运作,远离任何美学或道德关怀。
在通往地狱的入口和珍贵的手稿之后,参观者被邀请进入迷宫,自超现实主义以巴黎为中心的文学意象(如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1926 年创作的小说《巴黎人》(Le Paysan de Paris)、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1928 年创作的小说《娜佳》(Nadja)、菲利普-苏波(Philippe Soupault)1928 年创作的小说《巴黎的夜晚》(Dernières nuits de Paris))以来,迷宫这个神话般的地方不断出现。策展人以迷宫般的方式对展览进行排序,这种方式借鉴了超现实主义展览本身,尤其是 1938 年(巴黎美术馆)和 1947 年(巴黎 Maeght 美术馆)的国际超现实主义博览会。13 个关键词沿着超现实主义的主题,从最初的直觉和早期大师,到文学参考、政治定位和宇宙观,通过地点和氛围展开:Entrée des médiums、Trajectoire du rêve、Lautréamont、Chimères、Alice、Monstres politiques、Royaume des mères、Mélusine、Forêts、Pierre philosophale、Hymnes à la nuit、Larmes d’éros、Cosmos,这些是各部分的名称。展出的作品种类繁多,包括一些 “教科书式的杰作”--例如乔治-德-基里科(《爱的咏叹》,1915 年)、保罗-德尔沃(《L’Aurore》,1937 年)、马克斯-恩斯特(《La Toilette de la marie,1940 年)、萨尔瓦多-达利(Reve causé par le vol’une abeille autour d’une pomme-grenade,une seconde avant l’éveil,1944 年)、勒内-马格里特(René Magritte,L’Empire des lumières,1954 年)。但是,在超现实主义最著名的道路之外进行研究,并将其与早期人物以及在某些情况下与后来的情况重新联系起来的愿望,也使我们有可能探索那些不太著名的或人们意想不到会遇到的艺术家的作品。书中的路线密集而曲折,建议众多,每一个综合的尝试都很复杂,但又不遗漏任何片段,显然,只有将这些片段结合在一起,才能充分体现这场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就已经将来自 14 个不同国家的艺术家的研究结合在一起的运动。






展览的第一章名为 "媒介入口"(Entrée des médium),引用了布勒东 1922 年发表在《文学》(Littérature)上的一篇文章,探讨了超现实主义在媒介方面的起源。按照时间顺序,我们可以追溯到 1860 年,维多利安-萨杜(Victorien Sardou)的一幅象征主义蚀刻画《莫扎特的家》(La maison de Mozart)在此出现,而这一运动的公认大师之一也在此出现:前超现实主义 "大师乔治-德-基里科(Giorgio De Chirico)和他的代表作《纪尧姆-阿波里奈尔肖像》( )(1914 年)中,这位法国诗人化身为奥菲斯,戴着一副墨镜,象征着能够看到表象之外的世界。背景中,阿波利奈尔的轮廓上有一道伤疤,预示着多年后他脸上的伤疤会在受伤后出现。这个故事让德-基里科本人成为超现实主义者的千里眼。维克多-布劳纳(Victor Brauner)的《自画像 》(1931 年)也有类似的故事,在这幅画中,艺术家展示了自己没有眼睛的样子,而这只眼睛多年后才会消失。同样出自布劳纳之手的著名画作《Le Surréaliste》(1947 年)与赫克托-海波利特(Hector Hyppolite)的《Ogoun Ferraille 》(1947 年)并列展出。这两幅作品都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或多或少地提到了戏法家和巴戈特的奥秘,以及参观者后来在参观过程中遇到的塔罗牌世界。因此,他们的出现开始在参观者的脑海中勾勒出这一运动的地理边界:不仅是作为前卫艺术之都的巴黎,而且还包括欧洲,因为布劳纳出身罗马尼亚,后来通过收养成为法国人,还包括拉丁美洲,因为海波利特出身海地。
在艾琳-阿加尔(Eileen Agar)的《无政府状态的天使》(1936-1940 年)和伊迪丝-里明顿(Edith Rimmington)的《博物馆》(1951 年)等作品中,被剥夺的视觉打开了新的感知世界这一主题也再次出现。这两件由英国艺术家创作的作品,一件雕塑,一件素描,为蓬皮杜对超现实主义历史的深入研究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从一开始,该团体中就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女性组成部分。从 Meret Oppenheim 到 Frida Kahlo 的超现实世界》(法兰克福 Schirn 美术馆,2020 年)或《女性的超现实主义》(蒙马特尔博物馆,2023 年),第 59 届威尼斯双年展的标题就引用了 Leonora Carrington 的故事书《梦之奶》。为纪念百年诞辰,蓬皮杜在玛丽-萨雷(Marie Sarré)的帮助下出版了《魔法少女》(Les Magiciennes)一书。女权主义与女性魅力。Leonora Carrington, Ithell Colquhoun, Remedios Varo(2024),首次收集并部分翻译了这三位艺术家的一些文字。
在《Entrée des médium》一文中,布勒东再次写道:“我和我的朋友们知道[......]什么是超现实主义。[......]某种心理上的自动性,与渴望的状态完全吻合”。在 1924 年的《宣言》中,“梦 ”也是一个中心主题,并考虑到了它之前或同时代的医学和精神分析研究。布勒东说:“我相信,梦境和现实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状态在未来会得到解决,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这就是一种绝对的现实,一种超现实。我要去征服它,我确信我不会到达那里,但我对自己的死亡毫不关心,我不想以某种方式预示这种拥有的喜悦”。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在《交流的花瓶》(Les vases communicants,1938 年)中很好地表现了这一双重概念,这幅海报色彩强烈,笔触明显,是为布勒东在墨西哥大学的演讲而创作的。随后,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令人不安的作品(《Le rêve》,1931 年)、安德烈-马松(André Masson)充满活力和混乱的作品(《Dans la tour du sommeil》,1938 年)以及琼-米罗(Joan Miró)更具诗意的作品(《La sieste》,1925 年)都展现了 “狂欢 ”的意象。奥迪隆-雷东(Odilon Redon)的《闭眼》(Les yeux clos,1890 年)也是这方面的先驱。多拉-马尔(Dora Maar)的摄影蒙太奇作品(《无题》、《Main et coquillage》,1934 年;《Le simulateur》,1936 年)和格雷特-斯特恩(Grete Stern)的作品(《Sueño nº 17: ¿quién será?

![乔治-德-基里科,《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肖像[前兆]》(1914 年;布面油画和木炭,81.5 x 65 厘米;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 乔治-德-基里科,《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肖像[前兆]》(1914 年;布面油画和木炭,81.5 x 65 厘米;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https://cdn.finestresullarte.info/rivista/immagini/2024/2886/giorgio-de-chirico-ritratto-premonitore.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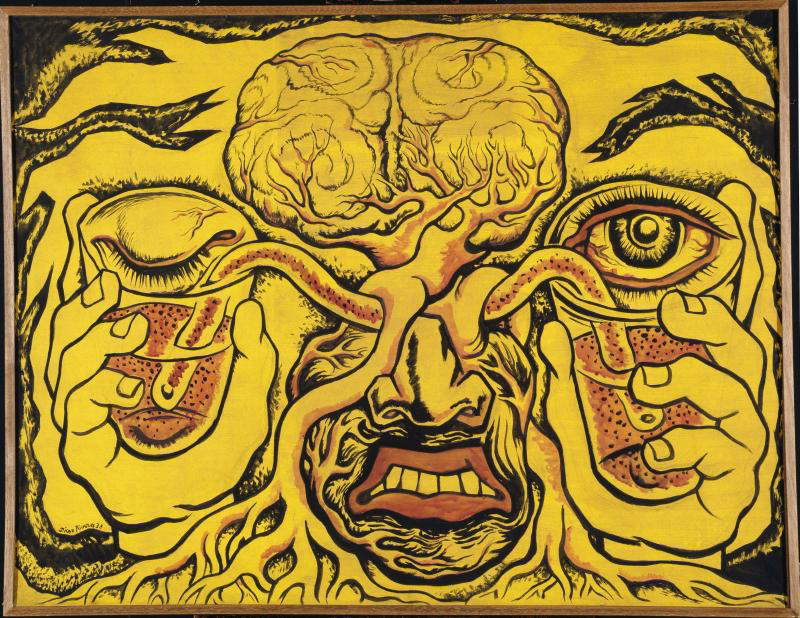


 多拉-马尔,《无名》[Main-coquillage](1934 年;摄影蒙太奇,40.1 x 28.9 厘米;巴黎,蓬皮杜中心)](https://cdn.finestresullarte.info/rivista/immagini/2024/2886/dora-maar-sans-titre.jpg)


如果说第一展厅展示的是超现实主义最著名、最广为人知的方面,即与作为梦境维度的超现实相关的方面,那么接下来的展厅则无疑是对超现实主义参考资料的倍增和丰富,所有这些展厅都配有丰富的文献资料,在少数情况下,还配有精选的电影片段(汉斯-里希特、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路易斯-布努埃尔)。根据诗人 Lautréamont(Isidore Ducasse 的笔名,超现实主义的启蒙人物)对 “美 ”的定义:“Beau comme la rencontre fortuite sur une table de dissection d’une machine à coudre et d’un parapluie”,自发并置的不协调和令人迷失的图像仍在继续。曼-雷(Man Ray)的作品(1932-1933 年)的标题就取自这句话,它与许多标志性物品并列,其中达利的《Le téléphone aphrodisiaque》(1938 年)和沃尔夫冈-帕伦(Wolfgang Paalen)的《Nuage articulé》(1937-2023 年)无疑最具代表性,此外还有阿尔贝托-贾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的雕塑/家具《Table》(1933 年)。早在 1925 年,超现实主义者就已经开始构思 "精致作品"(cadavre exquis)这一游戏:展览中的一些标本讲述了这一经验的运作过程,借鉴了最初应用于语言的程序,制作出个人天才被刻意压制的集体作品。从另一个角度看,成为超现实主义象征的神话人物奇美拉(chimera)也同样具有将不协调的元素结合在一起的含义。多萝西娅-坦宁的《生日》(1942 年)或许是展览中对这一主题最引人瞩目的表现之一。同样类似的还有布列塔尼心目中的传奇人物 Melusina,她是整个展览的标题,以人类与自然重新结合的名义,这个双名词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森林成为恐慌融合的场所,同时也是通往无意识的大门和新启蒙之旅的起点。这方面的诠释者包括马克思-恩斯特(La forêt,1927 年;Vision provoquée par l’aspect nocturne de la porte Saint-Denis,1927 年)、维弗雷多-林(Lumière de la forêt,1942 年)、约瑟夫-康奈尔(Owl Box,1945-46 年),以及超现实主义之前的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Frühschnee,1821-1822 年)。关于夜的主题,超现实主义宣言中从未提及,但却始终存在于表面之下,尤其是在矛盾而模糊的表象中,布拉萨伊的摄影作品(Statue du Maréchal Ney dans le brouillard, 1932;Quai de Conti, 1930-32;Jardin du Luxembourg, s.d.)探索了巴黎首都的一瞥,这已经是前述《Le paysan de Paris》中夜行的背景。
文学意象在超现实主义者的视觉提案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这也是一系列作品的基础,这些作品明确以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的《爱丽丝 梦游仙境》(1865 年)为主题,或受到重新发现德-萨德侯爵书页的影响。对于超现实主义者来说,卡罗尔的角色打破了逻辑思维的束缚,几乎成了他们的痴迷,也是他们后来重新创作和重新阅读的起点:雷内-马格利特(René Magritte)的《爱丽丝在梦幻国度》(Aliceau pays des merveilles,1946 年)抒情而梦幻,克洛维斯-特鲁耶(Clovis Trouille)的《爱丽丝的梦幻之旅》(Le rêve d’Alice dans un fauteuil,1945 年)夜色而阴郁,马塞尔-让(Marcel Jean)的《超现实主义衣橱》(Armoire surréaliste,1941 年)催眠而暗示日常物品世界,多萝西娅-坦宁(Dorothea Tanning)的《一个家庭的肖像》(Portrait of a Family,1954 年)则再次以社会和妇女状况为主题。爱情是爱神(Eros)和撒那托斯(Thanatos)之间永恒的对立,被视为一种自由、革命和丑恶的情感。例如,Toyen 的色情插图(Sans titre,1930 年)、Dali(Le grand masturbateur,1929 年)和 Félix Labisse(Danaé,1947 年)的令人不安的图像、Mimi Parent 的物品(Maîtresse,1996 年)或 Hans Bellmer 的 La Poupée(1935-1936 年)都证明了这一点。


在蓬皮杜艺术中心举办的超现实主义百年纪念展是巡回展览的一部分,该展览从布鲁塞尔的比利时皇家美术馆开始,将于 2025 年期间在马德里的马普瑞基金会、汉堡的艺术馆和费城艺术博物馆举办,每个展览地点都有特定的展期。这次深度游览占地面积超过 2200 平方米,从博物馆展厅延伸到超现实主义的象征性场所,以及展示超现实主义运动对当代创作影响的展厅。毕竟,这也是策展人希望在本次周年纪念活动中强调的主题,超现实主义在提供对 世界的新的解读和重塑世界的尝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它往往公开反对压迫性、极权主义 和殖民主义政治制度。伊夫-唐吉(Yves Tanguy)的画作《 妈妈,爸爸有福了》(Maman, papa est blessé),1927 年;《风》(Vent),1928 年;布劳纳(Brauner)的《母亲节》(Fête des Mèrescycle从展览项目本身的指导形象开始(马克斯-恩斯特,L’ange du foyer ou le Triomphe du Surréalisme,1937 年);怪物的宇宙,有时被解释为或多或少可识别的政治寓言;需要在科学与艺术之间找到新的调和;需要在艺术与科学之间找到新的调和;需要在艺术与科学之间找到新的调和;需要在艺术与科学之间找到新的调和。需要在科学与诗歌之间找到新的调和,因此将重点放在了炼金术上(Remedios Varo, Papilla estelar,1958 年);目光变得宽广,达到了对宇宙的憧憬,并渴望塑造一种更新的文明。超现实主义的 “更新”,也是从非西方模式中汲取灵感,重新思考和质疑人类和生物的地位,如《第三宣言或非宣言》(Prolégomènes à un troisième Manifeste ou non,1942 年)。
蓬皮杜艺术中心的超现实主义百年纪念活动(该中心即将关闭多年)是对这一运动的一次真正的重新沉浸,而这一运动往往被集中在少数几个人身上,并普遍被简化为欧洲范围的运动。此次展览是按照时间顺序在同一座博物馆内举办的其他深入的专题展览(2002 年的 "苏维埃革命“;2009 年的 ”颠覆图像“;2013 年的 ”苏维埃主义 与 艺术品“;2016 年的 ”艺术与自由")和专题展览的延续,同时还配有播客和 "苏维埃主义 与艺术品"系列丛书。该书附有一个播客,内容丰富,既有展览章节,也有对超现实主义重要主题的更精确的见解(例如,对全球维度、女性角色、政治愿景以及艺术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思考),对当今读者而言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本文作者 : Stella Cattaneo
Specializzanda in Storia dell'arte e valorizzazione del patrimonio artistico presso la Scuola di Specializzazione dell'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Genova. Attualmente curatrice di Casa Museo Jorn (Albissola Marina, Savona), ha partecipato a convegni e giornate di studio all'Università di Losanna e all'Università di Genova (2019) e a seminari internazionali di museologia (école du Louvre, 2018). I suoi interessi di ricerca si rivolgono prevalentemente all'arte contemporanea con particolare attenzione al periodo del secondo dopoguerra e all'opera di Yves Klein.免责声明:本篇意大利语原文的中文翻译由自动工具生成。 我们承诺会对所有文章进行审核,但无法保证完全避免因软件造成的翻译误差。 您可以点击 ITA 按钮查看原文。如发现任何错误,请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