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话进一步了解 Luca Pancrazzi(Figline Valdarno,1961 年)的艺术。在佛罗伦萨完成学业后,潘克拉齐前往美国,在那里他遇到了乔-渡边(Jo Watanabe),并在他的工作室为索尔-卢伊特(Sol Lewitt)创作图形和壁画。1992 年之前,他一直在罗马为 Alighiero Boetti 工作。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他一直致力于对艺术媒介、其影响、错误的创造可能性以及技术和材料的综合利用进行分析研究。大都市空间和景观,以及它们与界定它们的人类目光之间的连续性,是他最认真研究的主题。他通过绘画、素描、摄影、录像、环境装置、雕塑、与其他艺术家的共同行动和出版项目来表达自己。他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举办展览,并从 1996 年开始受邀参加一系列国际展览,包括威尼斯双年展(1997 年)、维尔纽斯三年展(2000 年)、冠军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1998 年)、巴伦西亚双年展(2001 年)、莫斯科双年展(2007 年)和罗马四年展(2008 年)。展示过他作品的众多公共空间包括:P.S.1当代艺术中心(1999 年)、摩德纳市立美术馆(1999 年)、马里诺-马里尼博物馆(2000 年)、教皇宫殿(2001 年)、Revoltella 博物馆(2001 年)、Lenbachhaus und Kunstbau 美术馆(2001 年)、GAMEC(2001 年)、卢加诺州立艺术博物馆(2002 年)、Centro per l’ Contemporary Art Luigi P. P.Contemporary Art Luigi Pecci (2002)、Zentrum Fur Kunst und Medientechnologie (2003)、PAC (2004)、MAN (2004)、MART Trento and Rovereto (2005)、MAMbo (2006)、Macro (2007)、越南国家美术馆 (2007)、Fondazione Pomodoro (2010)、Museo per Bambini di Siena (2010)、Palazzo Te (2016)、Santa Maria della Scala (2023)、Gallerie degli Uffizi (2024)。他在米兰生活和工作。

GL.卢卡,对许多艺术家来说,童年都是属于艺术世界的症状的最初表现,对你来说也是这样吗?
LP.所有艺术家,甚至是我所认识的非艺术家,都有过童年。随着我对他们以及我自己的了解加深,我发现每个人都有一个或多或少美好的童年。那么多富有创造性和艺术性的童年,他们的童年本该如此,没有日后充斥他们头脑的模式。艺术家的条件是意识到并决心成为艺术家,而童年则是没有意识和觉知的自由条件。这种意识只能属于以后的时期,一个学习和形成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人的建构处于批判世界的阶段,同时也爱上了这个世界。创造和破坏是青春期的一部分,在这一阶段,焦虑可以转化为认识和决心的条件。在这一时期,性领域,正如我们现在所说的性别领域,不断经历着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刺激风暴,在这种流动的、岩浆般的意识运动中,形成了日后将要建立的存在结构。我还记得,我放弃了早年想成为一名纪录片导演的愿望,却从未尝试过成为一名纪录片导演。我在孩提时代就已经开始摄影,先是模仿父亲拍摄的姿势和照片,然后记录家庭出游,后来又在自己拍摄的照片上绘画。但是,你所说的’属于艺术世界’的意识仍然无法存在。我心目中的艺术家是一个孤独的人,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能够将童年的自由延长到青春期和少年期,然后对成人世界充满希望。如果说我开始对艺术世界有了一丝归属感的话,那很可能是在所有这些纯粹的愿望结束的时候,所以那一定是一个现实失望的时期。这一切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逐渐发生的,年复一年地与现实发生冲突,把我带离童年,寻求自主。这种新的社会条件所带来的困难让我意识到自己处于社会的边缘,因此我需要从中找到力量,才能继续生活下去。时至今日,我仍然觉得自己处于社会边缘,同时也处于艺术体系的边缘,我不确定自己是否曾经属于这两者,就像你在问题中理想化的那样。
在你讲述的这段旅程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重要的好或坏的大师?
当我能够自己选择的时候,我就进入了佛罗伦萨的艺术学校,那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在佛罗伦萨市郊的那所中学里,我遇到了有准备、有深度的老师。我的绘画老师是那些年我学习绘画的第一个重要参照点,在他的指导下,我学会了辨认当代艺术和艺术的展示场所,我们会去看展览,他会带我们去他的工作室,事后我可以说,他是一位大师,也是一位好老师。在佛罗伦萨学院学习的那些年,除了几位出色的老师,绘画课程一直被一个无法给学生提供教导和参考的人物所困扰。后来,我有幸结识了两位艺术家,并为他们工作,我的人生从此翻开了新的篇章。我在纽约和罗马为他们工作,为其中一位工作的时间和为另一位工作的项目交织在一起,然后我离开了佛罗伦萨。两位截然不同、截然相反的大师,最终却殊途同归。
这两次相遇是如何产生的?是您以某种方式促成了他们,还是一切都是偶然?
用 A.和 B.的话来说,我的回答是 “事情的发生是必然和偶然的”。
不久前,您告诉我另一次重要的会面,即与玛丽亚-路易莎-弗里萨的会面。你们是何时、如何相识的,玛丽亚-路易莎在将您引入艺术体系方面发挥了怎样的重要作用?
我与玛丽亚-路易莎-弗里萨相识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佛罗伦萨。在那个年代,佛罗伦萨是一座非常活跃和生动的城市,有趣的存在和艺术画廊为这座城市增添了活力,而这些在佛罗伦萨都是前所未见的。音乐、设计、时尚、艺术和实验戏剧是广场、中心剧院、地窖、夜晚、迪斯科舞厅和沙龙的主角。玛丽亚-路易莎-弗里萨(Maria Luisa Frisa)是艺术和文化生活的中心,她创办了一份期刊,并策划了对我的成长至关重要的项目和展览。在那段时期及以后,我们经常来往,后来就失去了联系。1989 年,我在佛罗伦萨乡间的一栋老别墅里建立了自己的工作室,这栋别墅因被遗弃和荆棘丛生而得以保存下来,我们组织了一次艺术驻留活动,邀请了主要来自米兰和佛罗伦萨的艺术家同行。对我来说,这是一种雏形,多年来我通过各种合作项目不断培养这种雏形。比斯提奇城堡是一次共享时间和空间的体验,在这种参与式实践中实现了作品。展览是一个附带活动,结束了欢乐的部分。在没有策展项目的情况下共聚一堂是我们的目标,在没有保护和过滤的情况下参与其中是我们的实践。在最后的聚会上,我记得玛丽亚-路易莎-弗里萨(Maria Luisa Frisa)和我们一起分享了这一时刻,我们一起想出了通过当时和我们在一起的摄影师的眼睛和他的笔来记录所发生的一切的可能性,他在一本临时制作的小册子上留下了证词,这本小册子后来被印刷了出来。






您在 Vivita 画廊举办的首次展览也是由您负责的,是吗?
有两个朋友邀请我参加在 Campi Bisenzio 的马尼拉迪斯科舞厅举行的社交活动中的比赛,后来我和他们一起在街头创作了一幅作品。结果我玩得很开心,我们的涂鸦颇具表演性和激进性,在 Vivita 画廊里又创作了一幅涂鸦。玛丽亚-路易莎-弗里萨(Maria Luisa Frisa)也是该奖项的评委之一,因此她间接地参与了我们这个团体的维系工作,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个团体一直以 “意大利进口”(Importè d’Italie)为名开展活动。与佩德罗-里兹-阿-波尔塔(Pedro Riz’ A Porta)和安德烈亚-马雷斯卡尔基(Andrea Marescalchi)一起,我们继续在混合环境中开展活动,以这个集体名称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艺术和表演活动。
在佛罗伦萨乃至整个托斯卡纳地区,正如您之前提到的,那些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您经常接触的艺术家有哪些,你们之间是否有争论,争论的主题是什么?
这是在经历了 “紧缩 ”时期和 20 世纪 70 年代的 “领先年代 ”后产生的结果。从创造力及其他角度来看,20 世纪 80 年代是一个复兴时期。这是私人和机构实现全面数字控制之前的最后一段快乐时光,我们现在正经历着这一时期,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我们将看到数字控制植入我们的生活。当时的世界是模拟机械和磁性的,工匠充斥着意大利的各个城市,郊区的生产技术也在不断创新,同时保持着高质量的产品和精湛的工艺。那时,我住在佛罗伦萨,在佛罗伦萨乡间有一间工作室,还经常去美国旅行,并在那里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在佛罗伦萨,我经常与我这一代以及上一代的艺术家们打交道,而上一代的艺术家与新一代的艺术家之间的关系有些可疑。在罗马,我在A.和B.的工作室工作,画廊老板和经纪人从那里经过,我们一起去看他那一代艺术家的展览,然后在开幕式上认识年轻的艺术家。我经常从佛罗伦萨出发,参观艺术家朋友在博洛尼亚和米兰举办的展览,尤其是在画廊开幕式上。在纽约,我曾在索尔-卢伊特作品的工作室工作过一段时间,结识了一些与那个世界接近的艺术家。
在纽约,我曾在为索尔-卢伊特制作作品的工作室工作过一段时间,在那里我认识了几位与那个世界接近的艺术家,他们的世界围绕着渡边的印刷厂,墙上画作的色彩配方就是在那里设计的。最接近我们的艺术家之间的争论,是我们在揭开当代艺术秘密的同时,享受前卫艺术和运动终结的壮观景象的粘合剂,这种自由感令人陶醉,而且往往是分散的。艺术家的数量很少,我们用手就能数出他们的名字,我们参考了前几代大师和艺术家的作品,并试图在技巧、洞察力和创造力方面超越他们。
你们是成功摆脱对立面和文化政治化负担的第一代人,因此能够更加自由地在各种语言之间穿梭。马西利奥-马尔基亚基(Marsilio Margiacchi)和卢西亚诺-皮斯托伊(Luciano Pistoi)无疑是这些新实例的第一批接受者:您是如何认识他们的,与他们之间建立了怎样的关系?
无论是否被分拆,我们过去和现在都一直承受着巨大的个人压力,尽管在那些年里画廊和评论家们各行其是,但我们还是试图独立行事,因为急躁的我们找到了可能和不可能的方式来展示我们的作品。有一天,安东尼奥-卡特拉尼(Antonio Catelani)向我介绍了一位来自阿雷佐的小胡子画廊主,他很有好奇心,愿意为年轻艺术家们提供帮助。阿雷佐一直是一个沉睡的小镇,坐落在乡间,处于纵横交错的托斯卡纳和意大利旅游大篷车的边缘,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迎来第一次工业发展,使佃农和农民成为市民和工匠,提高了社区的经济水平。我们和一小群艺术家,包括曾与我一起在佛罗伦萨高中学习的吉安卢卡-斯盖里(Gianluca Sgherri)一起,开始频繁出入马西利奥-马尔吉亚奇(Marsilio Margiacchi)的画廊,他先是让我们打扫画廊的陈设,然后热情地参与展览策划,与意大利所有的新艺术家展开合作。在搬到米兰之前的那段中间时期,我搬到了阿雷佐乡下一栋不寻常的乡村工业建筑里,几乎每天都能与马西利奥一起直接跟踪项目进展。事实上,我们和他一起来到了位于基安蒂中心的沃尔帕亚(Volpaia),一个来自都灵的社区在那里定居并创建了一个艺术中心。卢西亚诺-皮斯托伊在沃尔帕亚筹备了一年一度的展览季开幕活动,这是最早的定期艺术活动之一,利用了整个村庄的环境,然后让社区参与最后的庆祝和开幕活动。艺术界人士、评论家、艺术家收藏家、艺术爱好者、记者、画廊老板和学生从四面八方赶来。1992 年,我和来自意大利各地的跨代艺术家一起参加了一次活动,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与皮斯托伊和马尔贾奇度过了美好的时光,谈论艺术和其他事情,评估艺术家,策划展览,卢西亚诺经常参观阿雷佐的画廊。




玛丽亚-路易莎-弗里萨在 Margiacchi’s 举办的第一个展览是一个群展,象征性的标题是 “变化”,这个标题取自您在目录封面上发表的一件作品。除了吉安卢卡-斯盖里(Gianluca Sgherri),安德烈亚-桑塔拉斯奇(Andrea Santarlasci)也和您一起参加了展览:阿雷佐探险的后续活动是什么?
Cambioin pratica 展览是一个无标题展览,以封面上的作品命名,是与其他艺术家一起选择的。这次展览是马西利奥画廊的分水岭,从那时起,画廊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年轻的新艺术家身上:这一变化必然涉及到重新定义展览空间,使其适应形式整洁和无陈设的新要求。几年后,我在与马尔科-辛戈拉尼(Marco Cingolani)的一次展览中也用它做了一件作品,这是一次双个展,我把地板翻到了天花板上,并在上面挂上了画作。画作描绘了从天花板上俯瞰前一次展览中的人们。然后,连棕色地毯也消失了。1991 年,我们不仅在阿雷佐展出,还在佛罗伦萨的 Palazzo della Provincia、罗马的 Sala 1 画廊、米兰的 Corrado Levi 工作室展出。1993 年,我与摩德纳的 Galleria Mazzoli 开始了长达数年的合作,同时还与 Galleria Continua 合作。第二年,我把工作室搬到了米兰,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
您目前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最近,我在绘画和素描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因为我总是创作一些周期性的作品,而这些作品往往来自时间上相隔很远的其他周期。我遵循一条合乎逻辑的主线,然后我又准时地失去了这条主线;我试图保持连贯,但又准时地背叛了自己;我试图把重要的事情牢记在心,但又准时地用徒劳无益的事情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我试图理解我的作品产生了什么,但又准时地通过专注于细节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我试图有一条连贯的道路,但又准时地背叛了自己的期望。这是我得到的教训,也是我付诸实践的东西。
档案是否是您重拾上述背叛机制的一种方式?
档案是一种方法,背叛是一种防御,如果你想介绍档案的主题,我可以告诉你一些对各种挪用方法的痴迷是如何转化为收集,然后存档的。图像是人类的遗产,即使它们受到版权保护。我收集它们,并将它们编目。我收集多个主题,对它们进行挑选,然后丢弃其中的许多,摒弃其中的一些,将它们变为液体,用各种可能的方式进行绘画或印刷,将它们印在脑海中。例如,我收集 20 世纪 80 年代的星星、印有星星的图片、旗帜的细节、将军和军人外套上的勋章、帽子上和旗帜上的装饰、横幅上的装饰、印在路人 T 恤上的装饰,这些都是从任何杂志或报纸上剪下、撕下的图片中捕捉到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作品越来越多,它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 “星星系统”,一个独立的作品。在出版的图片中,从不缺少明星的身影,他们是摄影标准中真正的连续体,他们在任何时期都非常时髦,军人、恐怖分子、运动员、电影明星,他们都自豪地展示着自己,并通过他们的印刷图片将他们带入我的档案中。 除了明星图片,我的档案中还有许多其他主题,分为不同的类别和主题,都按字母顺序存档。随着时间的推移,档案变成了一种方法,它被自动喂养,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准时导致它的背叛,如果它是培养出来的,它就会被抛弃,如果它是存在的,它就会被躲避,如果它是不可或缺的,它就会被排除在外。
除了编目和收集您感兴趣的图像,您是否还将您的作品存档?
档案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是一回事,而档案作为作品和材料的组织又是另一回事。几年前,我创建了卢卡-潘卡拉齐档案馆(A.L.P. Archivio Luca Pancrazzi),这是一个实体场所,收集所有作品、摄影文献、传记和书目文件、目录以及作品周围的一切。这是一个用于摄影、编目、包装、拆封和存档的空间。
那么,回到最初的几件作品,利用档案馆的优势,我想请您重点谈谈几件作品的起源和后续作品的发展。第一件作品是在 Volpaia 展览会上展出的透明气动体积作品《收集空间》,第二件作品是与马尔科-辛格拉尼(Marco Cingolani)合作举办展览时在马尔吉亚基画廊(Galleria Margiacchi)天花板上制作的装置作品。
收集空间 “是指空旷的空间,这是我为 1992 年在托斯卡纳沃尔帕亚举办的 ”Spendente "展览而创作的作品的原名和含义。
我想通过谈论一个像虚无空间一样不可能拥有的物体,来突出收藏意义的矛盾性。这件作品考虑到了村子里的一部分实际空间,将其切割出来,简单地揭示出来,并通过一个透明聚氯乙烯充气装置进行展示,该装置是通过精确追踪连接小村庄自发城市发展中两个小广场的人行地铁内部空间的建筑结构而建造的。我感兴趣的是两座建筑之间的那部分空隙。那座雕塑只不过是对我们周围空隙的揭示。为了突出它,我需要一个外壳来容纳和限定它。该项目是通过使用充气技术实现的一系列项目中的第一个,它试图通过反向扫描,考虑到空的部分而不是我们习惯于评估的经典的完整体积,来揭示世界本质之间的关系。底片阅读扫描世界,揭示隐藏的东西,而空洞则向我们讲述实体,揭示它们,就像我们第一次看到它们一样。Volpaia 的作品是在两个小方块之间焊接成地铁形状的大型透明 pvc 管。我们按照尺寸制作,粘合得非常好,一充气,我就发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太阳光从一端照射到管子上,光线越过了 PVC 的厚度,整个管子被反射的光线照亮,变成了一块冰。当时,我正在以不同的方式从空洞的体积和空间中构建形式和图像,因此,即使是 Volpaia 展览中的蜡像也不过是复制空洞形式的铸模,以形成新的体积。同一时期,在马尔基亚奇画廊举办的双个展中,我得以突出我们周围和我们所居住的空间的另一个方面。我与马尔科-辛戈拉尼(Marco Cingolani)共同举办了这次展览,他利用当时的一个主题创作了一种受伤宇航员的图像雕塑。在他的作品中,主题是宇宙,是宇航员探索的空间,对我来说,玩弄空间的概念特别有用,即使在我的作品中,是玩弄画廊本身的空间。地球空间与宇宙空间的关系。这个装置的设计源于费德里科-福西(Federico Fusi)之前在画廊举办的展览,当时我在天花板上安装了一台摄像机,用遥控器遥控,从天顶视角拍摄所有的人。一些注意到这个装置的人抬起头,我就能拍到他们脸部朝向观察者的不寻常姿势。我用这些照片制作了 11 幅画作,悬挂在天花板上,之前还在地板上铺了一块像地毯一样的棕色帆布。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对称的、上翻的空间,在我的展览期间,画廊的新参观者可以观察到这种上翻,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经常会有被摄者在天花板上观察自己的翻转。空间和时间是中间的粘合剂,也是展览的主题,同时空间也成为宇宙和宇航员戏剧的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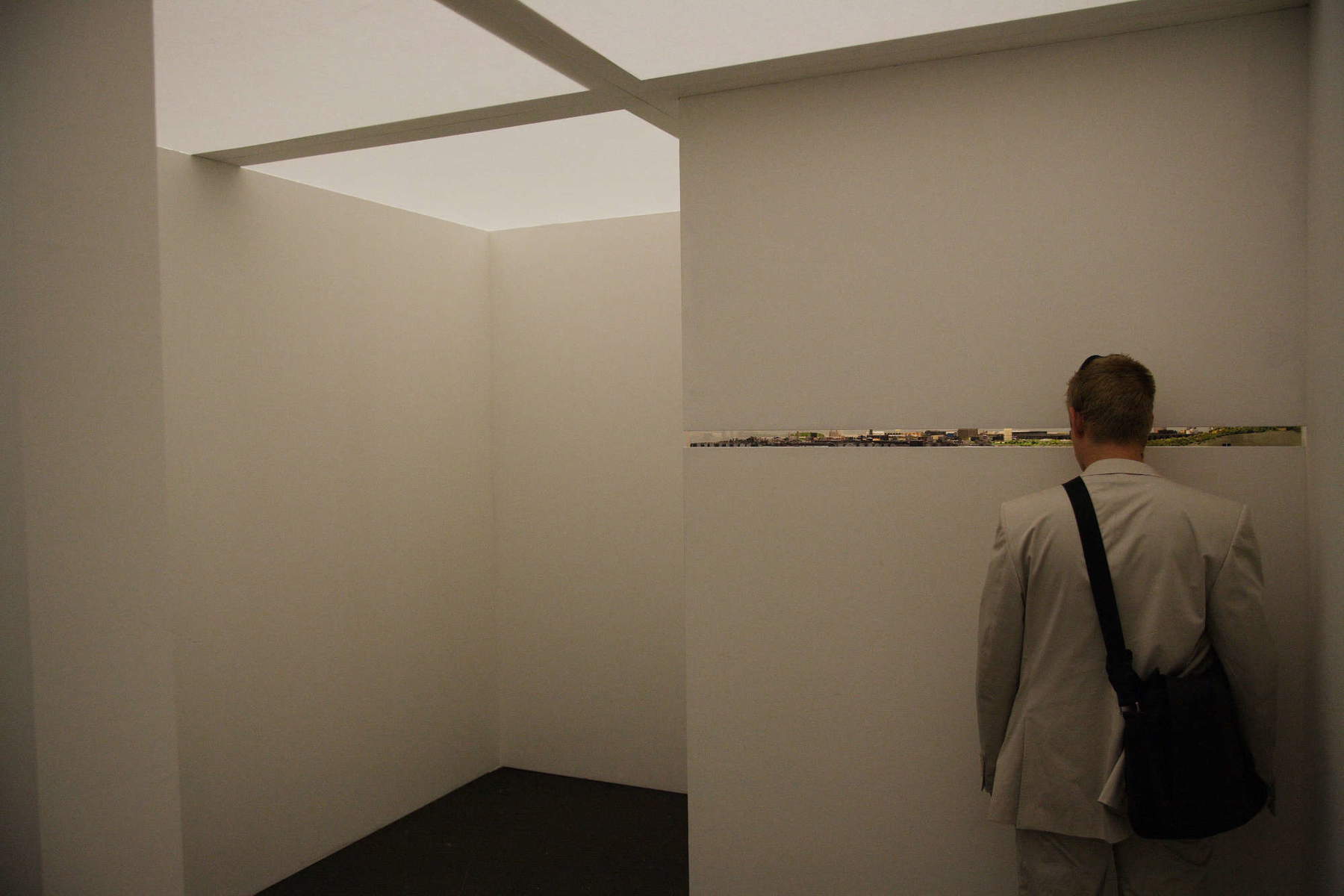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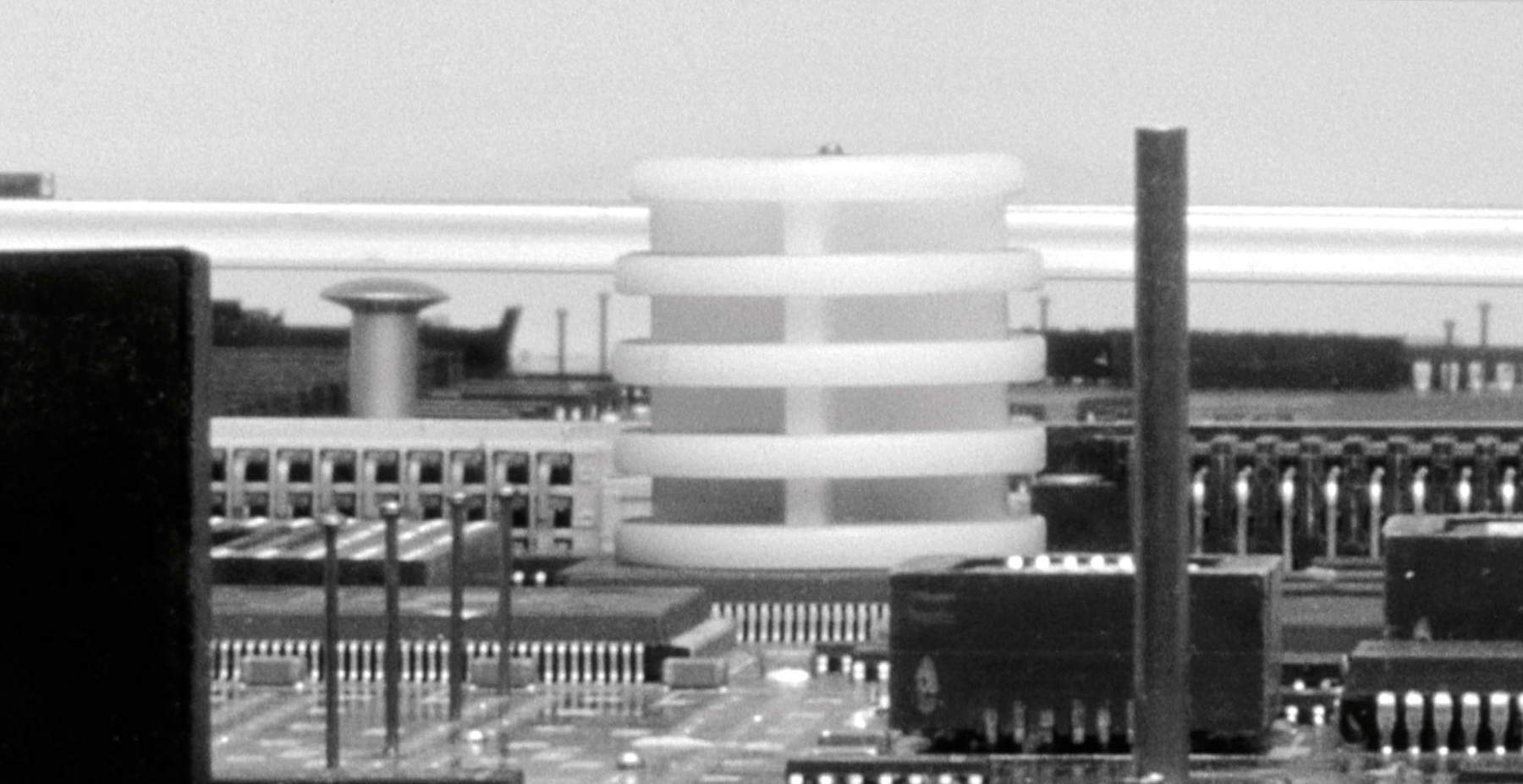
空间和时间这两个元素在您的作品中占据着中心位置,而且您一直以来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对它们进行审视。在我看来,另一个具有凄美色彩的元素是游戏性,这或许源于与 A. 和 B. 的紧密联系:您能谈谈吗?
二十世纪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为开端,标志着整个世纪的到来。我出生于 1961 年,正值经济和实证主义蓬勃发展之时,对我们时代的确定性提出质疑是一种语言使命,也是反对即将到来的一切的日常实践,而且已经是最清醒和最愤世嫉俗的预感的结果。波普艺术、观念艺术和情境主义属于我们,就像最糟糕的后先锋派绘画属于今天的年轻艺术家一样。我们是这个星球上最后一批 “过一天算一天 ”的居民,在电子技术诞生以来社会控制的车轮上插上了一根辐条,我们的活动是为了躲避让地平线上的天空变得漆黑晦暗的巨大未来的锋芒,但 “过一天算一天 ”既是维护自由的自然防御,也是反对的工具。时间和空间是爱因斯坦的线性。空间是无限的,但还不是弯曲的,而量子力学虽然诞生于同一世纪,但比相对论稍晚一些,爱因斯坦本人也曾对其提出过质疑,并将等待新世纪来更好地接受、检验和普及。游戏及其规则对我来说是一种智力锻炼,我从小就和哥哥一起制作新游戏,部分是利用其他东西,规则的构建是最复杂、最有趣的部分,游戏随后用于微调和验证。我们玩了很多游戏,在我们的小房间里,在后来成为我第一个工作室的同一个房间里,我们生活在游戏中,在那里我继续发明和生活在其他类型的游戏中。然后,语言卡伦布尔、谜语、谜语都是语言的一部分,也是继续玩艺术的方式。它们总是或多或少地从我的作品和经常与我合作的艺术家的作品中的窗户和前门进入。当时与 Boetti 在他的作品中的合作无疑加强了这一方面,并给了我必要的安全感,使我能够继续为这一实践留下优越的位置。
早些时候,当您谈到 “收藏空间 ”时,您着重描述了光线在 PVC 透明材料上的反射,这不可避免地让人联想到绘画,这是您作品的另一个要点。我想请您深入探讨一下这方面的问题,比如告诉我们白底画是如何创作出来的,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您在这方面的创作是如何发展的......
正如我一直所说的那样,我是一名艺术家和画家,我的艺术创作以视网膜方法为主,即使是雕塑和三维空间也是如此,但在这种情况下,我认识到控制会时不时地被减去。绘画仍然是一扇窗,当这扇窗被打破、被砸碎、没有玻璃、有碎玻璃、关闭并拉下百叶窗,或者像整座由玻璃制成的房子一样大时,这扇窗就是这扇窗户是绘画在形式和观念上的慰藉,是画家们不可或缺的主要参照物,绘画一直是艺术的主要环,是窗户成为了另一种东西。这个世界 在画廊的空间里,在城市的空间里,在世界的空间里,引发了一种不可避免的分形关系,成为所有绘画的主题,在无限的反射和交叉引用的游戏中,同时保持在一个有限制的空间里。对于画家来说,在这个空间中,存在着控制的可能性和野心,或者说,一切都产生了通过物质的混沌试图进行控制的设定。画家自认为是混沌的创造者,对其失败或成功负责。但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受欢迎的是那些走出绘画空间的练习,这些练习逐渐使人倾向于将注意力转移到纸张和画布的边缘、厚度和背面......然后,画作搁置在地板上,纸张被抛向空中,画布被刺破,表面被撕裂,画布被从画框上取下,重新糟糕地组装起来,出现褶皱和一次性的丰满,颜料并没有停留在画作的边缘,它继续在墙上、地板上,它走出门外,在人行道上漫步,它在立面上膨胀,变成气体,在空气中着色无休止地消失,随着情绪的低温凝结,再次冻结成三维形式,石化或液态树脂记忆,从街道重新进入前门,甚至从窗户进入房间。所有无法控制的事物都会以超致命的方式失去控制。这个移动的世界与画作接壤,使画作被包含、被吸纳,所有这些外部元素都是画作总量的一部分,成为一个完整的装置。因此,画家们通过这种广泛的意识,获得了一种现代野心,即需要控制展览的装置空间,控制节奏和绘画周围的陈设配件、踢脚板、地板、光线,当然,我们不应忘记,绘画是在另一个地方绘制的,在那里这种中立性是不存在的。当然,我们不应忘记,绘画是在另一个地方绘制的,那里不存在这种中立性,绘画如果不是在特定地点进行,就会在工作室的混乱中诞生,这是一种有机的混乱,四分五裂的艺术家通过他的内脏将这种混乱散布到或多或少准备好并经过消毒的画布上。因此,我也觉得自己是一个被现实世界军事化了的画家,我把完全控制周围空间的雄心壮志留给了不同周期的作品。我一直偏爱自然光,因为它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在一天中不断变化,在日出和日落之间的演变过程中,它变得温暖或寒冷,在云彩飘过时,它突然变暗,它通过这些周期性的变化传达了时间和不稳定性的概念。我非常喜欢自然光的变化,为了充分体会这种变化,我多年来一直在夜间工作,使用投影仪放大图像,这样我就可以开着窗户欣赏黎明的到来,结束一天的工作。在黑暗中,眼睛会训练自己适应微弱的光线,大脑会通过这些微光完成重建世界的动作。在黑夜中,形体通过光线显现出来。因此,我开始从最基本的、必要的开始画画,通过白色来限制形式的构建。同样的白色与粉笔混合在一起,用来为画布提供背景。在这个准备空间里,我开始并完成了绘画,由于缺少颜料,暗色部分便显露出来。然后,自然的画布就是背景色调,通过按顺势剂量稀释颜料,我创作了风景画和静物画。我最近在纽约举办的展览以光为主题,展览目录在一年多之后已经出版。"闪光灯"这个标题强调了与这种表现相关的方面,将其引向光在某些情况下造成的眩光、反射和对比。
眩光的概念让我想起了您的另一件作品,那辆覆盖着透明玻璃碎片的玛莎拉蒂,您在其他物品(钟表、椅子......)上也采用了这种做法,这些物品是您标志性作品的一部分。这些作品也是在研究光吗?
所有东西都在研究光,甚至是黑暗。以 “rundum ”结尾的系列作品暗指碳化硅材料,因此被命名为"(car)borundum“。我希望它能在佩斯卡拉巡回展出,1996 年,在 ”Fuori Uso “展览期间,第一件作品 ”Carborundum "在佩斯卡拉巡回展出。在这第一件作品中,我采用了后来用于本系列作品的技术。我想用汽车上不易碎的玻璃碎片覆盖汽车。我希望玻璃珠能在宏观上模拟研磨材料的功能,同时又能发光。这件作品必须像用于制造磨片和磨料的碳化硅那样具有研磨性,而且必须像玻璃那样能够反射光线,以打破物体的紧凑形态,并通过反射使其破碎,就像我的白色颜料产生它所代表的形状一样。研磨光的碎片就像盖德布兰德形势派出版物的磨砂封面每次取出并重新放入书柜时,都会消耗掉附近的书籍一样,我的carborundomised汽车在穿过城市时,也会磨平、磨掉所有的角落和粗糙,使事物和房屋变得光滑。在佩斯卡拉的那些日子里,一场风雨肆虐了当地大型玻璃公司的露天仓库。因此,我免费获得了难以想象的大量玻璃,最重要的是,我可以从各种碎玻璃中进行选择。因此,我改变了最初使用防碎玻璃的计划,转而使用更具威胁性的透明玻璃碎片。我选择了厚度较大的玻璃和超清玻璃,它们粘在汽车上的牢固程度远远超过了墙顶上的玻璃,使其无法通行。我的 Regata 涡轮增压发动机非常漂亮,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定制车,一天晚上我在佛罗伦萨的一家酒吧里这样告诉 Lapo Elkan。
玛莎拉蒂是他提供给你的?
不,是让-托特好心提供给我的,当时他要求一辆法拉利,哪怕只有车身,也要涂成红色,带轮毂,但他把要求改成了一辆全新的旅行用四门玛莎拉蒂。后来,我把莫斯科双年展的设计从废弃的穆拉诺红色玻璃换成了厚厚的美国超级透明玻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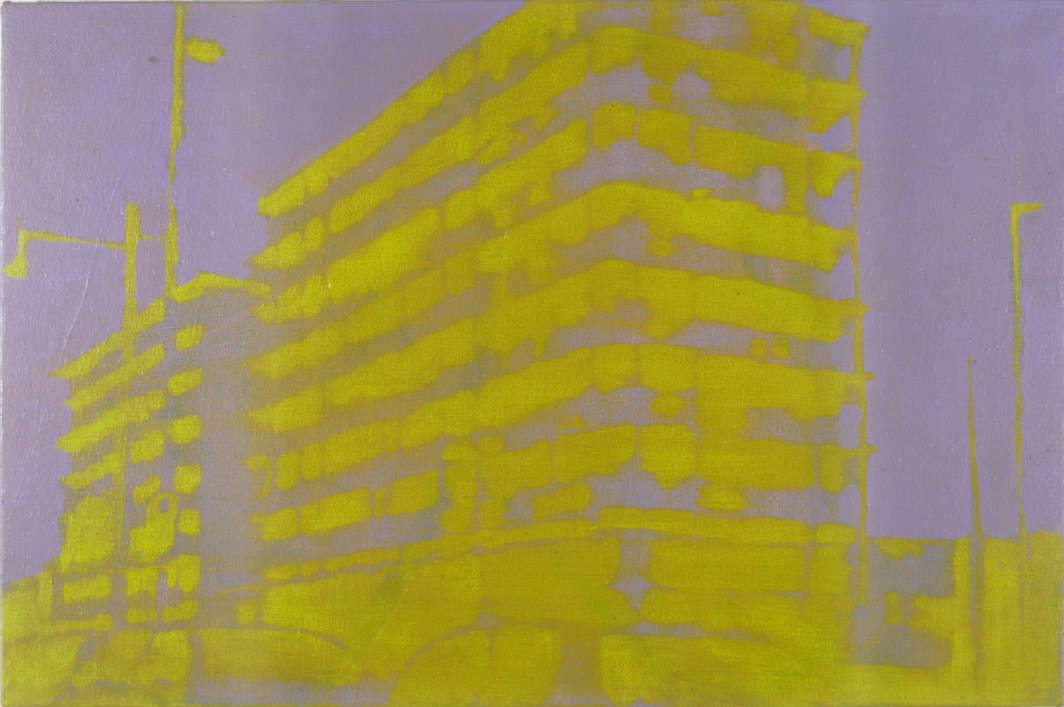






在这里,我想问您,在您的作品中,玩转再现尺度的想法非常重要,比如从 1/1 到微景观。
从一件事到另一件事......我想您提到了 2007 年莫斯科双年展上的展览 "1:1",您还提到了为地平线而创作的一系列雕塑,在某些情况下,这些雕塑采用了建筑立柱的形式,在视平线处插入了一幅风景画......您对此有何评论?游戏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它是创造和解构的引擎。在将不同尺度的作品并置在同一作品中的过程中,我通过让人无法看清作品、用实际的建筑尺度来伪装作品,同时强加一种近距离观察的方式来制造眩晕感,从而使背景消失。观察者必须积极地将自己与作品和空间联系起来。空间看起来是空的,有墙、有地板、有柱子。其中一根柱子上有一个奇怪的切口,为了更好地理解,人们走近它,切口就在眼睛的位置,但柱子怎么会被切掉呢?切口里面是什么?你必须走得更近,把眼睛贴在那个切口上,最后我们看到的是一幅风景画,一幅让人联想到风景画的地平线,因此我们透过柱子本身,看到了切口之外的空间,柱子之外的空间。空间的使用就像是在一个空旷的建筑空间中穿梭,同时地平线上的景观形象已经在我们的脑海中形成。作品《风景观察着我们》就是在这种不平衡和眩晕中完成的。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风景是由小碎片组成的,这些小碎片是停留在观察平面上的物体。一个钉子、一个螺栓、一盒大头针、一个卷笔刀、一个计算器键盘变成了建筑物、水塔、烟囱、工厂,构建了一个属于用一些现成物品唤起的共同愿景的景观。没有任何建构,这些物品被粘在槽中,绕着圆柱走一圈,就能从四面八方看到三维景观。景观是什么?它是由什么构成的?观察者会改变景观本身吗?两个不同的人看同样的风景,看到的东西一样吗?远眺地平线一直是对眼睛和心灵的良好锻炼。
城市景观通常是您作品中的主角,是什么吸引您选择这些非地点?
城市景观并不意味着非场所。自从马克-奥热(Marc Augé)在他的文章《非场所》(Non-lieux)中分析了景观中存在的关系减弱的空间,即所谓的非场所。Introduction à une anthropologie de la surmodernité》(1992 年)一文 中分析了景观中存在的被称为 “非场所 ”的关系减弱的空间,自此,我们开始意识到,漫无边际的人类化创造了功能取代关系的稀缺空间。这些新认识到的空间已成为我们星球的一个特征。城市景观是我每天都要去的地方,我学会了解读城市的变化和细微差别,我从一个中心到另一个中心,沿途都有优越的基础设施通道,将所有中心无缝连接起来。我认为,你在我的作品中发现的非场所,就是那些代表场所之间沟通的走廊和空间的画作。我开始画走廊 ,因为它们没有自己的艺术家来表现和提升它们。我是第一位尝试表现关系稀疏空间的画家,也就是说,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那些反绘画的地方,却没有给它们一个表象。其中许多画作实际上并不是非场所,而只是通道、交换和交流的场所。这些画的总标题是 “室内”,因此对我来说,它们是对木板油画的致敬,是绘画中的作品,是表现建筑内部的绘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图标选择逐渐趋向于上述空间,这些空间最初来自偷来的图片,来自办公室面板和模块的目录,来自预制和层压建筑构件,来自某种国际功能主义的玻璃和室内隔断。被称为 “Interni ”的画作在很短的时期内可以与奥热创造的这个词相提并论,但在此之前和之后,它们完全变成了另一种东西,甚至某些周期的静物画也是在工作室现场绘制的。这种对某些稀有空间的诗意表现,在以中心对称视角描绘的公路和高速公路以及隧道和桥梁系列中得以延续。另一方面,城市景观并不是一个非场所,至多就郊区而言,我们可以说这些地方趋向于匿名性,趋向于某种程度的统一性,但它们并不是非场所,我想说它们是卓越的场所,是人类悲剧的空间,当我们将自己投射到景观的视野中时,它们可以唤起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这可能就是它的意义所在,我们所观察到的任何事物都有其神圣之处,这取决于我们用什么样的眼光和意愿去观察它。

本文作者 : Gabriele Landi
Gabriele Landi (Schaerbeek, Belgio, 1971), è un artista che lavora da tempo su una raffinata ricerca che indaga le forme dell'astrazione geometrica, sempre però con richiami alla realtà che lo circonda. Si occupa inoltre di didattica dell'arte moderna e contemporanea. Ha creato un format, Parola d'Artista, attraverso il quale approfondisce, con interviste e focus, il lavoro di suoi colleghi artisti e di critici. Diplomato all'Accademia di Belle Arti di Milano, vive e lavora in provincia di La Spezia.免责声明:本篇意大利语原文的中文翻译由自动工具生成。 我们承诺会对所有文章进行审核,但无法保证完全避免因软件造成的翻译误差。 您可以点击 ITA 按钮查看原文。如发现任何错误,请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