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毫不讳言,在踏入 巴勒莫阿巴泰利斯宫地区美术馆(2019年1月4日)的门槛之前,我对由乔瓦尼-卡洛-费德里科-比利亚(Giovanni Carlo Federico Villa)策划的安东内罗-达-墨西拿(Antonello da Messina)展览抱有很高的期望,该展览于2018年12月14日开幕,将持续至2019年2月10日。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人们对它的期望越来越高:它有望成为仅次于2006年在Scuderie del Quirinale举办的伟大展览和2013年在罗韦雷托Mart举办的展览的 “年度展览”、“2018年巴勒莫文化之都日历上的旗舰活动”、“几乎一半的安东内罗-达-墨西拿作品都会展出”。在安东内罗-达-墨西拿(Messina,1430-1479 年)的亲笔作品展上,我本以为会出现与佛兰德斯和威尼斯语言的图标、风格反思和图像关系,或者更好的是与当代雕塑和肖像画的关系,这些都在阿巴泰利斯的永久收藏(免费)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其中之一就是弗朗切斯科-劳拉纳(Francesco Laurana)。1953年在墨西拿赞卡宫(Palazzo Zanca)举办的展览(安东内罗-达-墨西拿和西西里400年的绘画,目录由乔治-维尼(Giorgio Vigni)和乔瓦尼-卡兰丹特(Giovanni Carandente)编辑,朱塞佩-菲奥科(Giuseppe Fiocco)作序,卡洛-斯卡帕(Carlo Scarpa)排版)是一个研究视角,该展览展示了大师的18幅作品以及活跃于14至15世纪的画家的作品。该展览由萨尔瓦多-普利亚蒂(Salvatore Pugliatti)担任执行委员会主席,费尔迪南多-博洛尼亚(Ferdinando Bologna)、费德里科-泽里(Federico Zeri)、斯特凡诺-博塔里(Stefano Bottari)、切萨雷-布兰迪(Cesare Brandi)和朱利奥-卡洛-阿甘(Giulio Carlo Argan)等学者参与其中。不仅是杰作展,还有对艺术家背景和文化环境的思考与重建:另一个例子是1982年的墨西拿展览 "四世纪西西里的文化"(1982年2月20日至3月7日)和地区博物馆的安东尼奥-达-墨西拿展览(1981年10月22日至1982年1月31日),由亚历山德罗-马拉博蒂尼(Alessandro Marabottini)和菲奥雷拉-斯里奇亚-桑托罗(Fiorella Sricchia Santoro)策划,是安东尼奥活动的一部分。我们可以说:巴勒莫展览错失良机。
早在 2018 年的头几天,展览就已宣布举办,并大肆宣传,引起了新闻界的共鸣,但实际上,展览被证明是一个“莫(n)紧张的事件”,包含了许多疑虑。在我的这番反思结束时,我们可能会洗个现实澡,意识到这次展览在组织和科学角度上都存在缺陷:各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联系,其中一个因素的缺失(或者说:不足)导致了另一个因素的失败,形成了连锁效应。2018 年 1 月宣布的展览地点和展期是最原始的混乱:前者是萨利纳斯考古博物馆,后者计划从 2018 年 10 月 26 日开幕至 2019 年 2 月 24 日,长达四个月。这一切在阿巴泰利斯这个更合适的地点和推迟两个月并将开幕时间减半(从 2018 年 12 月 14 日至 2019 年 2 月 10 日)后都烟消云散了,这一决定可能隐藏着更深层次的动机。
 |
| 安东内罗-达-墨西拿展览的阿巴泰利斯宫入口处 |
 |
| 展厅 |
为了证实 “活动 ”的科学性和特殊性,在秋季的几个月里,出现了各种声明和新闻报道,宣布来自科莫(市民博物馆的《Annunciata ’Advocata virgo’》)、罗马(博尔盖塞别墅的《Ritratto d’uomo》)和都灵(玛达玛宫的《Ritratto d’uomo》)的作品将参展:只有后两幅肖像画才有助于解读《塞法卢肖像画》,因为它在展览行程中被单独安排在一个小房间里,与展览中的另一幅肖像画(帕维亚市政博物馆的《男子肖像画》)没有任何关系和对话。此外还宣布了 国际借展,如卢浮宫的《柱子上的基督》和伦敦国家美术馆的《书房中的圣杰罗姆》,后者已于 2006 年赠予墨西拿地区博物馆,以交换两幅卡拉瓦乔作品。只有这两件杰作,尤其是《圣杰罗姆》,如果真的来到巴勒莫, 才会赋予展览意义。值得回顾的是,2006年的墨西拿展览将伦敦的画板与圣格雷戈里多联画(有签名并标有1473年的日期)、乳白画板与圣母子、圣方济各会信徒和怜悯中的基督联系在一起,并进行对话西西里大区在佳士得拍卖会上购买了这幅画,同时还购买了锡拉库扎贝洛莫宫大区博物馆的《圣母领报图》,该博物馆当时因修复工作而关闭。这次拍卖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其目录由 Gioacchino Barbera 编辑,包含 Fiorella Sricchia Santoro、Lionello Puppi、Francesca Campagna Cicala 和 Giovanni Molonia 撰写的文章。
但回到广受赞誉的贷款,它们去哪儿了呢?漫步展厅,却找不到它们的踪迹。在展览开始的第一个展厅(因为《圣母领报》和《教会三博士》一直在其永久性位置,与展览没有任何重要的联系),人们立即注意到安东内罗的两件杰作 “存在/缺席”:《圣吉罗拉莫忏悔》和《三位天使在阿布拉莫的探视》(1465-68 年),这两件作品来自雷焦卡拉布里亚市立博物馆。售票处前的图腾上贴着一张 “通知”,上面写道:"安东内罗先生和夫人被告知,展览行程中将 没有绘画作品。在 “纪念性展柜 ”内,两块展板被 “下周起展出作品的照片复制 ”的信息所取代。从开幕式当天(2018年12月14日)起就出现了这样的字眼,而在我参观的当天(2019年1月4日)又再次出现了这样的字眼,当时除其他事项外,展览目录(19欧元)也没有出现。
 |
| 安东内罗-达-墨西拿,《圣母领报》(约1476年;板上油画,45 x 34.5厘米;巴勒莫,阿巴泰利斯宫,地区美术馆) |
 |
| 安东内罗-达-墨西拿,《带着祝福的孩子和一名方济各会信徒的圣母》,右侧(1463 年;画板上的钢笔画,16 x 11.9 厘米;墨西拿,地区美术馆) |
 |
| 安东内罗-达-墨西拿,《圣母领报》(1474 年;布面油画,180 x 180 厘米;锡拉库萨,贝洛莫宫) |
 |
| 安东内罗-达-墨西拿,《圣母领报》,细节 |
 |
| 安东内罗-达-墨西拿,《圣母领报》,细节 |
我找到了直接的消息来源:我电话联系了雷焦卡拉布里亚市民艺术馆馆长阿莫德奥博士,他对整个事件有清楚的了解,并向我证实,由于申请借出这两幅作品的时间过于紧迫,在 技术和行政上遇到了 困难和延误。市文化局批准了这一申请,但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处理和运输这两件作品,以及申请的时间安排上仍存在困难。在这一点上,皮纳科特克馆馆长自己也承认,这两块展板永远也到不了巴勒莫,因为它们现在距离关闭还有四周的时间,而它们的落成典礼已经过去了近一个月。因此,可以想象,最初的开幕日期从 10 月推迟到 12 月,其原因可能是某些借展(如卢浮宫和国家美术馆的借展)未获批准,以及组织上的疏忽(如来自雷焦卡拉布里亚的展板)。
一个疑问出现了:除了出售图录(仅从 2019 年 1 月 6 日起出售)的收入外,售票处的全部收入归谁?负责售票的 Vivaticket 公司和展览组织公司 MondoMostre 之间是否有协议或谅解备忘录,后者 “既提供资助、组织和推广活动的全套服务,也提供售票、交流、推广、创建特别晚会和寻找赞助商等一系列服务”?是 MondoMostre 还是阿巴泰利斯的科学管理部门发出借展申请并决定入场费?鉴于作品的缺席,门票价格显得相当高:全票 13 欧元,减价票 11 欧元,团体票 11 欧元,周末团体票 13 欧元,团体和个人预售 2 欧元。
 |
| 未参展作品的照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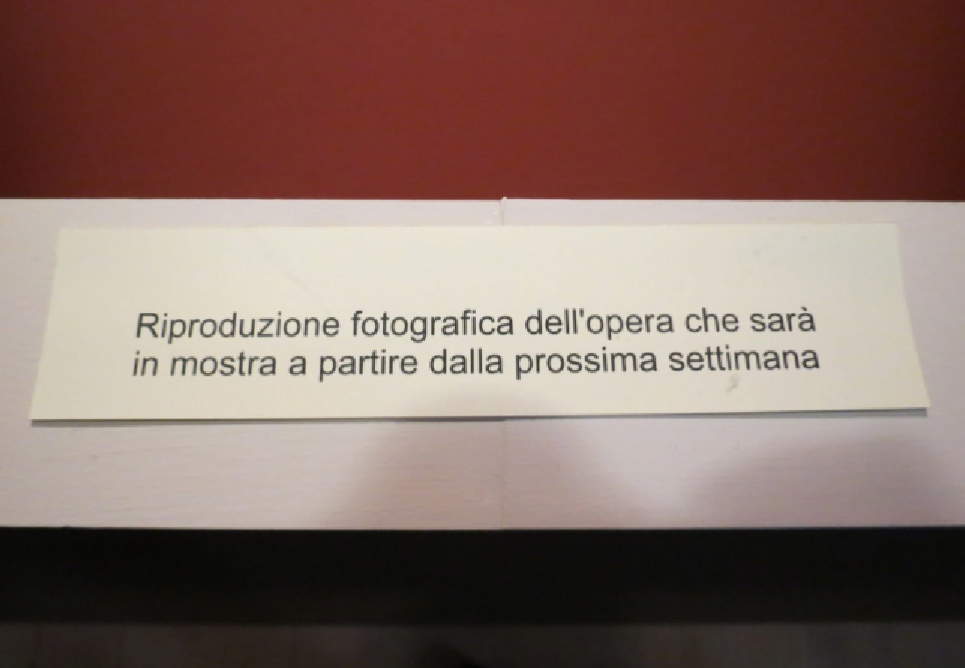 |
| 上述照片附带的标志 |
 |
| 左图,贝洛莫宫展出的《圣母领报》(在箱子内)。右图,在巴勒莫展览上展出的作品 |
这些都是合理的问题,同样合理的问题是,是否真的值得将《圣母领报》从锡拉丘兹贝洛莫宫地区美术馆的背景中连根拔起,这件作品存在各种保护问题:1693 年的地震使其受损,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潮湿腐烂,1914 年,为了粘在画布上,原木支架上的漆膜被撕裂。在贝洛莫宫,这件作品被放置在一个保持湿度和温度指数以及环境微气候条件不变的灵龛中。而现在在阿巴泰利斯展出的作品却没有任何保护措施,也没有任何保持稳定环境值的元素,而乌菲齐美术馆的《圣母子、圣约翰和圣本尼迪克特》多联画却有这种保护措施。此外,根据地区委员会 2013 年第 94 号和第 155 号决议,“构成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和藏品主要资金 ”的不可移动资 产中的一件珍贵作品,正是由于其微妙的地位,才被列为锡拉库扎作品。根据 2013 年 6 月 27 日第 1771 号评估法令通过的 2013 年第 94 号和第 155 号地区委员会决议,该作品与阿巴泰利斯的《报喜鸟》和墨西拿的《圣格雷戈里奥多联画》一起被列为 “构成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和收藏馆主要基金 ”的不可移动资产。从贝洛莫宫运出这幅画时的处理方式和运输过程(根据网上公布的视频录像和新闻文件)可能对作品不利,其精细程度本应导致以更高的批判意识进行评估,以避免胶水、支撑物和画膜之间的强制和紧张关系。我不想再回过头来看这些文章,也不想再回过头来看那些坚持操作的绝对科学性和作品存在的必要性(几乎是强制性的)的人与那些正确地提出保护和保存问题的人之间的来来回回的争论,事实证明,这些因素都是有根据的。
简单数了一下,在被宣称和宣传的15件作品中,也就是臭名昭著的 “安东内罗的一半作品 ”中,有4件没有出现在名单上(即两件来自雷焦、卢浮宫和国家美术馆的作品),而不少于4件来自阿巴泰利斯的永久收藏(《 圣母经》和三位教会博士);实际借出的安东内罗的作品只有7件,除此之外,还有安东内罗从贝加莫卡拉拉学院借出的雅各贝罗创作的《圣母与圣婴》画板。
有鉴于此,托马索-蒙塔纳里(Tomaso Montanari)的小册子《Contro le mostre》(Einaudi, 2017)中的一段话似乎很有启发性,也很贴切:“随你怎么称呼它们:票房展览、大片展览、包罗万象的展览。它们的成分总是一样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都是一般的、似是而非的、肤浅的。平庸、琐碎、甚至无用、有害,以展示一些众所周知的 ”战利品 “为基础,将其转化为空洞的偶像:偶像符号。曾经有能力表达确切含义的绘画作品失去了其语义和象征意义的深度:它们沦为(充其量)只能提供模糊视觉满足感的物品。我们可能会说 ”这是一种邪恶的流行病“,这与切萨雷-布兰迪(Cesare Brandi)慷慨激昂的 ”我控诉“(j’accusement)如出一辙:”我们正被文化价值极低或毫无文化价值的活动展览的泛滥所包围,这些展览都是以短暂的奇观为目的。昙花一现的壮观本身就是目的,’可回收的空壳’人为地诱发了拜物教式的消费,五颜六色的肥皂泡实际上什么也没留下"。
免责声明:本篇意大利语原文的中文翻译由自动工具生成。 我们承诺会对所有文章进行审核,但无法保证完全避免因软件造成的翻译误差。 您可以点击 ITA 按钮查看原文。如发现任何错误,请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