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月 15 日在比萨大教堂歌剧院开幕的展览在某些方面是一次方法论上的赌博,或者说是一次同义反复。事实上,如果有一座建筑不等着被展示,因为它甚至是在所谓的奇迹广场的草地上向无数游客展示的,那正是比萨大教堂的钟楼。对建筑的直接感知,显然被那些通过报纸、网站和连环画中的插图所中介和间接呈现的感知所压倒。多年前,一项并不精确的计算表明,斜塔是网络上最受欢迎和搜索次数最多的古迹之一,仅次于罗马斗兽场。
此外,钟楼上没有任何隐藏的艺术品,也没有那些被楼梯和圣器室的黑暗所掩盖的不为人知的珍宝,就像宫殿和教堂中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即使是众多雕刻精美的柱头(有人称之为 “由柱子组成的塔”),也可能会让最挑剔的人失望,因为现在,这些柱头都是很早以前就开始更换的,到 19 世纪结束时,工匠们拆除了最后一批损坏的柱头,并用复制品取而代之,有时是忠实的复制品,但通常都是慷慨重新诠释的结果(但展览中出现了比杜伊诺(Biduino)创作的少数几个幸存的柱头)。
因此,我们所研究的主题是间接的,即与通天塔本身并无太大关系(不过,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也是一个涉及到的主题),而是如何看待和表现通天塔。这条路线从纪念碑的第一幅确定的图像开始,包括羊皮纸上的一幅图画,在这幅图画中,塔楼被清晰地表现为其第一位建筑师在 12 世纪离开塔楼时的高度,这证实了工程的中断是真实的,也许被解释为是确定的,因为塔楼有一个大屋顶。这也是展览的出发点,因为正是为了研究最近由朱利亚-阿曼纳蒂(Giulia Ammannati)为博纳诺-皮萨诺(Bonanno Pisano)修复的这座塔的自传这一引人入胜的问题,高等师范学院的讲师专门用了一个章节来介绍。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铁塔从一开始的描绘,我们就会意识到,从 14 世纪起(即铁塔完工之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几乎不可能找到单独描绘铁塔的图画,如果有的话,也是以两种截然不同但又相互连接的方式来描绘的。铁塔高耸入云,主宰着整个城市,成为城市中最具辨识度的元素;铁塔倾斜,与大教堂并列,让人联想到其本质上的宗教功能。托伦蒂诺的圣尼古拉斯从瘟疫中拯救比萨的非凡板画就是如此;16 世纪早期一位不知名艺术家的雕刻作品也是如此,虽然微小,但却是最基本的,城市展示了 1509 年被佛罗伦萨人摧毁的塔楼,但比萨斜塔却被突出地展示在中央,以其毫发无损的外形记录了其近乎象征性的价值。正如乔治-瓦萨里(Giorgio Vasari)为维奇奥宫中的比萨桥(Presa di Pisa)所绘制的图画一样,铁塔是这座城市的重要描述元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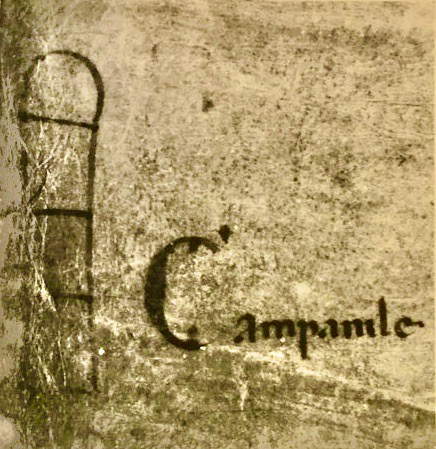




锡耶纳艺术家文图拉-萨林贝尼(Ventura Salimbeni)1603 年创作的一幅美丽的画作《比萨寓言》也向我们展示了一位面容黝黑的妇女,她的脸上带着抑制不住的悲伤,一心一意地吮吸着孩子们的乳汁,而摆放在她面前的武器的惯性却在她的脸上留下了痕迹。而她脚下武器的惰性表明,重新发现的财富是和平的果实,而这位身着长袍、举手投足间流露着基督教仁爱美德的妇女正是比萨,她终于能够养活自己的公民了,这要归功于那些说服她放下武器的人的慷慨解囊。因为在背景中,比萨斜塔和大教堂,以及人才花瓶(Vaso del Talento),构成了决定性的阅读暗示。
即使到了世纪之交,佛罗伦萨画家贝内代托-卢蒂(Benedetto Luti)仍然坚持以塔为主题,就像修辞学中的人物一样,暗示着整体。展览展出了这位佛罗伦萨画家早期创作的精美画作,这幅画曾被认为已经失传,几年前才在一个重要的私人收藏中被发现,它诠释了抽象的亲比萨知识分子的愤怒,他们在 17 世纪和 18 世纪之间坚持共和家园的模糊理念,而这个理念是如此的美丽和迷失。在这幅自 18 世纪以来首次向公众展出的巨幅画作中,马略卡岛的代表向胜利者致敬,胜利者是一位坐在宝座上的妇女,她的形象被大胆地添加到画作中,与背景中的比萨斜塔一起变成了比萨。
因此,比萨斜塔不仅是比萨的象征,也是这座城市的徽章。18 世纪末,在比萨的阿卡迪亚人圈子中,可能有卡洛-哥尔多尼(Carlo Goldoni)这样的正统知识分子,但也有容易玩文学游戏的文化半梦半醒者。18世纪末,弗朗切斯科-帕斯库奇(Francesco Pascucci)绘制了《特洛伊战争》,他是一位环球旅行画家,也是不乏文化内涵的小古典主义的主角,在这里,被希腊人围困的城市被高高的垂直城墙所封闭,虽然城墙没有中世纪的高大,但却足以掩盖斜塔高耸入云的存在。比萨因此变成了荷马史诗中的城市。
同样,斜塔也成为了这座城市宗教传统的象征和标志。在乔瓦尼-巴蒂斯塔-坦佩斯蒂(Giovanni Battista Tempesti)的画作中,圣拉涅利(Saint Ranieri)--这座城市的守护神--忧心忡忡地祈祷着,仿佛沉浸在一场不乏 18 世纪优雅风格的骚动中,为右侧的斜塔和大教堂留出了空间。在一幅较早的画作中,可能是皮斯托亚的多梅尼科-皮亚斯特里尼(Domenico Piastrini)所作,天使们陪伴着守护神恳求圣母保护这座城市。
在确定了塔楼在民用和宗教上的双重意义之后,展览试图解释从 18 世纪开始,这座建筑是如何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表象转变,这场转变与人们观念的改变相对应,当时塔楼开始从广场的其他部分中分离出来,就好像它是一座自成一体的建筑。从根本上说,这并不自相矛盾,这是一种将钟楼纪念碑化的形式,钟楼似乎失去了所有的宗教和民事功能,变成了一个大胆而罕见的美丽模拟物,其斜坡的耀眼而复杂的魅力丰富了钟楼,使其成为自己的纪念碑。由于版画(一般为蚀刻版画)的传播,这种转变尤为明显,版画的质量(如范布里尼和纳西奥的作品)时好时坏,而其他作品则品味一般,价格低廉。在一幅作者不详但复制程度很高的版画中,塔楼甚至失去了圆柱形的外观,柱状平面变成了完整的墙壁,这使得塔楼不是更接近于钟楼,而是更接近于罗马著名的塞蒂佐尼奥(Settizonio):因此是纪念碑中的纪念碑。




这一过程始于 18 世纪,并非偶然,因为建筑的去神圣化是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这些需求来自于着迷的公众,他们渴望将比萨斜塔变成一种存在的印记和纪念品。大旅游时代。
手持贝德克(Baedeker) 的贵族和游客的需求标志着建筑观念的深刻转变:从钟楼到斜塔,从钟楼到斜塔,从钟楼到斜塔,从钟楼到斜塔,从钟楼到斜塔,从钟楼到斜塔,从钟楼到斜塔,从钟楼到斜塔,从钟楼到斜塔,从钟楼到斜塔。从钟楼到斜塔。正如弗朗哥-卢森蒂尼的小说《脚注》(Notizie dagli scavi)一样,当 “教授 ”最终站在哈德良别墅的遗迹前时,他非但没有理解其意义,反而迷失在一个没有依托和意义的时代,被时代和生活的混乱浪潮所席卷。只是在这里,这种无意义往往表现为一种模糊不清的背景喧闹。
因此,弗朗西斯卡-巴尔索蒂(Francesca Barsotti)决定在展览开幕式上设立一个展区,强调铁塔的主要功能,恢复其作为信仰和信徒时间标志的身份。
无独有偶,随着时间的推移,铁塔已成为某些习惯于玩弄大众形象的艺术家的癖好或标志,有时甚至因持续的视觉消费而变得破败不堪。展览记录了这方面的一些例子,如马格里特用勺子(或羽毛)支撑的铁塔,或哈林光芒四射的小人,更不用说未来派画家对铁塔的真正热情了。同样,在曼努埃尔-罗西(Manuel Rossi)策划的展区中,我们也用大量篇幅展示了自拍时代之前的强烈现象--照片,这里有精美的黑白展品。
不过,虽然展览并没有重点介绍最近的修复工作(这需要举办自己的活动),但不能不提到自 19 世纪以来为阻止铁塔倾斜度上升所做的尝试,以及最近为确保铁塔安全所采取的干预措施。如果说这些方案记录了人类想象力的古怪和妄自尊大,那么至少在其中一个案例中,这些方案甚至是令人发指的。一个孟加拉小女孩画了一幅不确定的、轻微的图画,建议不要触动铁塔,而是将地基下的泥土移走,以重新平衡铁塔的结构。
如果说展览的第一展厅是以在世的艺术家们(巴托里尼(Bartolini)、巴尔贝里(Barbieri)、卢切西(Lucchesi))如何以 Campanile 为主题来衡量自己为主题的话,那是因为展览还没有停止向我们展示新的东西。众所周知,这正是经典作品最深刻的魅力所在。
免责声明:本篇意大利语原文的中文翻译由自动工具生成。 我们承诺会对所有文章进行审核,但无法保证完全避免因软件造成的翻译误差。 您可以点击 ITA 按钮查看原文。如发现任何错误,请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