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达维德-里瓦尔塔(Davide Rivalta)的狮子中,准备进入罗马国家现代与当代艺术馆(Galleria Nazionale d’Arte Moderna e Contemporanea)的公众已经排了七年的队。这些狮子是反对被动主义的守护者,是随时准备对一切带有过去气息的事物发出怒吼的凶猛猫科动物,是渴望对灰尘、霉菌和老化张开大嘴的炽热野兽,是渴望撕碎光辉灿烂的旧油画,是渴望唤醒沉睡的公众。那是过去的味道,炽热的野兽急切地张开大嘴,抵御灰尘、霉菌和岁月的侵蚀,撕碎光辉灿烂的旧画布,唤醒沉睡在这些大厅里的画家和雕塑家的公共宿舍。Hic sunt leones,本应如此:狮子的使命是在游客跨过博物馆的门槛后,向他们展示未被探索的艺术领地。然而,它们却站在那里,漫不经心地在美术馆的台阶上滚动,毫无攻击性,就像它们现在正凝视着 "未来主义时代 " 展览的横幅一样。策展人加布里埃尔-西蒙吉尼在新闻发布会上毫不讳言:"未来主义时代 “是一个面向所有人的展览,适合从 ”最狂热的藏书家 “到 ”追求科技新奇的孩子“,从 ”沉思爱好者 “到多媒体装置爱好者的广大观众。他保证说,新奇之处将出现在目录中,主要涉及《1909 年宣言》(乔瓦尼-利斯塔(Giovanni Lista)进行了新的诠释)和未来主义奇观主题(利斯塔与冈特-贝豪斯(Günther Berghaus)进行对话时提供了新的数据)。目前,展览目录尚未出版:因此,要对展览进行评估,而又不耽误太多时间,只需参考巡回展览即可。相反,这里没有新意,没有实质性的新意:西蒙吉尼说,”我们选择的是一种用户友好型未来主义,我们可以套用策展人的话说,这是一种老少皆宜的未来主义,我们举办的展览 “不仅仅是给业内人士看的”,“展览的主要目的是让人们了解未来主义的革命范围及其与当时和现在生活的联系:我很自豪能为所有人举办这样一个展览”。根据展览的理念,“与当今生活的联系 ”将体现在未来主义与科学、未来主义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上。
马里内蒂会喜欢 “每个人的未来主义 ”吗?他会喜欢科林斯式圆柱和粉刷过的房间之间的未来主义吗?他是否希望他的革命可以通过罗马通行证旅游票进入?马里内蒂可能获得赞赏的问题,在此时此刻,尤其是在敌视政府的文化圈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但这似乎是空谈:太阳落山后,每一个前卫艺术的命运都是成为资产阶级或历史,或两者兼而有之,无论如何都会成为过去(更何况我们对过去的态度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事实上,战后的马里内蒂或许会对前部长桑吉利亚诺的积极行动表示钦佩:马里内蒂在宣言《意大利未来派提出的艺术权利》(I diritti artistici propugnati dai futuristi italiani)中写道,政治革命 “必须支持艺术革命,即未来主义和所有先锋派”。桑吉利亚诺一定是完全领会了马里内蒂的意图,因为从他在罗马学院就职的那一刻起,他就一直在参与确定博物馆的内容。这是他第一次公开亮相时就梦想的(那是 2022 年 10 月 29 日,就在他上任一周后,桑朱利亚诺就已经开始幻想未来主义展览了,也许会在那不勒斯的大厅里举办......)。......在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的大厅里举办!),两年前的 12 月,随着朱塞佩-西蒙尼尼的正式任命,展览开始成形。后来发生的一切众所周知,在此重提展览筹备过程中的所有争议似乎毫无意义(从“......对于在新闻发布会上出现的观点,即即使是争议的蛛丝马迹也会唤起未来主义的氛围,无论如何都值得回答的是,未来主义者以毫厘不差的精确度寻找、提出和策划了争议,而不是像在格南展览上那样受制于争议):最后,潜伏在报纸专栏中的阴影变得有血有肉,幻想变成了实质,梦想变成了现实,展览展览终于到来了,它向所有人开放,向爱好者的鉴赏开放(这一点不会缺乏),向讨论和批评开放,随时准备接受辩论和权衡,带着它那巨大的材料负荷(五百件物品,其中三百五十件是艺术品,排列在二十六个展室中!Gnam 的负责人 Renata Cristina Mazzantini 甚至在新闻发布会上将其称为一个划时代的展览,即 ”可能是意大利近十年来最重要的展览"。
那么,如何评估展览的重要性呢?仅凭巡展路线上所安排的作品数量是不够的(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即使是那些从未涉足过博物馆的人也不例外),也没有必要强调借展的国际性,甚至往往仅凭展览所展出作品的质量也是不够的。如果缺少基本的元素,如果项目不明确,如果某些解读似乎是被迫的,如果装置是微不足道的,如果缺乏实质性的新颖性,缺乏新的外观,缺乏新的想法,甚至连组成展览的作品的质量也不够。因此,如果一定要根据其重要性来评价《未来主义的时代》 ,那么目前在罗马至少有几个展览无疑更为重要,即在 Scuderie del Quirinale 举办的关于卢多维西教皇的展览和在 Galleria Borghese 举办的关于詹巴蒂斯塔-马里诺与艺术的关系的展览,这两个展览都是以真正的新项目为基础,充满了相关作品和多汁的国际借展,深入探讨了很少或根本没有探讨过的主题(如果不是在文学领域,肯定是在展览领域)。然而,我们也必须从未来主义运动展览的历史角度来看待Il tempo del Futurismo 的 重要性。当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情况都是如此,但早在三十多年前,人们就开始拆除 "该死的记忆"(damnatio memoriae )所设置的障碍,如今,人们谈论未来主义的方式与谈论 16 世纪的方式主义或威尼斯的维杜特主义(Vedutism)完全相同,即未来主义是艺术史上的一个时刻。从这一角度来看,尽管伴随着展览发生了一些事件(11 月初,文化委员会在回答 曼齐议员的问题时毫不犹豫地指出,减少最初计划的作品数量--大约有六百件--不足以 使展览取得成功。必须强调的是,“西蒙尼尼教授本人与艺术部的政治领导层和国家现代艺术馆的管理层共同决定”(《未来艺术的历史》,第 2 卷,第 1 期,第 2 页)避免了意识形态或政治诉求。关于未来主义展览的历史,有人说,即使不必追溯太远,在最近的过去也有过一些更为激烈和重要的时刻:例如,比 Gnam 展览更具原创性的展览(仅限于意大利)有:Labirinto della Masone 的航空绘画展,甚至是2019 年的 Palazzo Blu 展览,该展览追溯了未来主义的历史(整个未来主义的历史,正如几年前纽约古根海姆展览首次完整地追溯了未来主义的历史一样),其章节与未来主义历史上的各种宣言相关联。去年出版的第一本关于吉诺-加利的专著,让人们注意到了巴拉的一位杰出学生,他的名字长期以来被掩盖在被遗忘的灰烬中。





那么,公众应该期待什么呢?在格南(Gnam)的房间里,正在举办一场可以被称为学术性的展览。说得大方一点,这是一个总结性的展览。一个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旁征博引的、简约的、循规蹈矩的、没有跳跃的展览。简而言之,这是一场传统的革命。这个展览也缺乏 “面向所有人 ”的初衷,因为展览中的设备被缩减到了最低限度,标明路线的几块展板上的信息也少得可怜,而且 Gnam 的一名员工告诉我,甚至连语音导览都无法收听:简而言之,这是一个面向所有人的展览,但实际上却几乎抛弃了公众。这并不是说展览缺乏重要作品,而是作为近十年来意大利最重要的展览,展览中存在许多缺失:例如,与 Pontus Hultén 于 1986 年在格拉西宫(Palazzo Grassi)举办的不可重复的展览中确立的四幅基本绘画作品(即 Boccioni 的《La città che sale 》、Russolo 的《La Rivolta 》、Carrà 的《I funerali d’Art》、Russolo 的《LaRivolta 》)相比,这次展览缺少了一些重要的作品、但在格拉西 宫只能看到一件作品,即鲁索罗的《反叛 》,这是一件真正意义上的特殊借展作品,它与巴拉的《Lampada ad arco 》一起或许值得整个参观过程。此外,博乔尼的《Rissa in the Gallery 》和《Footballer 》、巴拉的《Cane al guinzaglio 》和《Violinist 》、鲁索洛的《Profumo 》、航空绘画中的一些重要作品(如图利奥-克拉里的《Incuneandosi nell’abitato 》)、雕塑作品几乎全部丢失。这些作品与展览的其他作品在时间顺序上并不一致,因此公众在书卷、著作和文章中找到这些作品时,有可能低估了它们的相关性。西蒙尼尼在他的画册文章中提前对自己进行了甄别,将计算缺失作品(“这件作品在那里,但那件作品不见了”)说成是 “业内人士 ”的 “相当无聊的游戏”,但对于一个旨在成为 “艺术世界 ”的 “展示窗口 ”的展览来说,这种计算也许变得更加合理。不过,对于一个经过数月宣扬之后才开幕的展览来说,这种说法或许就变得更加合理了,因为它几乎是一个重生的事件,是 “国家美术馆本身的一个相关项目[......],多年之后,它又回来举办一个国际性的展览”。希望创始文本的出现并不是专家的 “onanism”:这通常是对具有相关性的展览的期望。
这显然并不意味着重要作品的缺失:判断也不应该过于偏激,这也是因为展览的开头确实很轰动,精致的第一展厅以小而密集的分裂主义基石唤起了未来主义的前提,佩利扎-达-沃尔佩多(Pellizza da Volpedo)的《太阳 与日落 》和塞甘蒂尼(Segantini)的《Alla stanga 》等作品与巴拉(Balla)的《Lamp ad arco 》进行了对话: 展览一开始就仿佛在告诉公众,在 20 世纪初,与自然节奏紧密相连的意大利乡村即将屈服于现代性的到来,屈服于城市的喧嚣,屈服于意大利的电灯。佩利扎的自然光减弱,巴拉的人造光升起,从此照亮了路线的其余部分。这是一个稠密而有力的开端,伴随着参观者走向另一个展厅,在这里展示着前未来派、其他伟大的分区主义者(尤其是普雷维亚蒂)和一些著名先行者的作品,尤其是罗莫洛-罗曼尼(Romolo Romani)的作品《迪娜 -加利的肖像》(Ritratto di Dina Galli ),以及《呐喊》(L’urlo ),这些作品悬浮在象征主义的回忆和对现代性的焦虑之间。
然后,在爆燃之后,展览开始失去力量、活力和强度,经历了一些时间上的错位(不仅是布拉加利亚的时间错位:最明显的是在一个仍然摆放着分裂主义和象征主义宣言的展厅里展出的汽车,首先是普雷维亚蒂( Previati)1913 年的作品《天使的堕落》(Caduta degli angeli ),该作品陈列在一辆玛莎拉蒂模型后面,而玛莎拉蒂是在普雷维亚蒂逝世 15 年后才问世的),以及在一个主要由格南(Gnam)藏品组成的展览中不可避免的稀释:即使在这里,也不乏值得一观的惊喜(巴拉的《未来派 》唤起了东方气息,法尔法的《马里内蒂的地理肖像 》,甚至伊沃-潘纳吉的《建筑功能 》。在未来主义的第二次浪潮中,他是另一种机械主义的支持者,其另一种机械主义具有强烈的政治含义),但事实上,展览的三分之一,粗略地说,是由东道主博物馆的藏品,尤其是其储藏室的藏品组成的(而且大部分重点是巴拉的作品,以及最后两部分关于 “未来主义 ”的继承或假定继承的作品)。未来主义的继承或假定继承),尽管参观者因有可能欣赏到原本难以欣赏到的作品而迸发出真诚的热情,但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会出现 “水土不服 ”的现象,一些基本的作品被淹没在众多外围作品之中,而且由于缺乏可以引导参观者的展板系统,这些作品有可能被忽视。尽管声称具有包容性,但被淹没在平面说教设备的浪潮中的有未来主义的《战争综合体》、朱塞佩-科米内蒂的《坎坎 》(他是分裂派中最令人感动的人物之一,也曾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一名未来主义者)、 巴拉的两件小型彩虹色 Compenetrations (这两件作品远非该系列中最好的,但却是该系列中最重要的),以及艺术家巴拉的作品。他以Compenetrazioni 将自己定位为欧洲最早的抽象主义者之一,根据最近的解释,他的抽象主义甚至早于康定斯基。Benedetta Cappa Marinetti 的摩托艇 和 Marisa Mori 的《Battaglia aerea nella notte 》(未来派女性对这一运动的贡献一直被忽视,尽管最近的研究已经开始提出这一问题,正如在 Labirinto della Masone 举办的展览中看到的那样)、Gino Galli 的《机械与动物活力 》(他是一位独创的、长期被忽视的未来派艺术家)、Benedetta Cappa Marinetti 的《Battaglia aerea n ella notte阿登戈-索菲奇(Ardengo Soffici)的用法国树液涂抹的灰泥自然 拼贴画,以及吉多-斯特拉扎(Guido Strazza)的两张画,他是唯一幸存的未来派画家,几乎被隐藏在航空彩绘部分。





据说,策展人希望展览的实质内容不是从在场或不在场者的登记册中产生,而是 “在一种文化’社会学’的背景下”,“首先是基于伴随其产生的基本科学和技术创新,没有这些创新,未来主义深刻而彻底的革命性意义就会完全消失”。当然,在众多关于未来主义的展览中,很难再想起哪一个展览不是坚持以机器或飞机为主题的,甚至连展出汽车和电器的想法也并不新鲜(1986 年的格拉西宫展览在这个意义上已经开创了先河)。让古列尔莫-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加入未来主义行列的想法同样值得商榷,尤其是展览试图强行将马里内蒂的想象力与无线电报的发展相提并论,而无线电报的发展为这位科学家赢得了 1909 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同年马里内蒂发表了第一份未来主义宣言。我们很难想象出一个未来主义的马可尼:如果我们想从另一个角度来回应,那么未来主义才是马可尼式的。事实上,我们可以根据克里斯波蒂的提示,想象出一个相反的马可尼,他实际上抑制了早期未来主义的电气神秘主义(如果我们愿意这样称呼的话),并将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未来主义者的研究导向了艺术与科学之间更密切的关系(《未来主义者的电车》)。Crispolti 写道:"有轨电车出现在 Boccioni 的《La città che sale 》的地平线上,同时也侵入了 Carrà 的画作。“街道、招牌、咖啡馆照亮了整个夜晚。O braccia dell’Elettrico / stretched out in every place / to take life, to transform it”,福尔戈雷在诗歌《L’elettricità》中唱道。这种震撼人心的新奇来自于神秘,它驱动着电机和电力,是早期未来主义的灵魂。但直到马可尼的天才逐渐赋予它其他魅力,并在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赋予它新的视角,它才变得普通起来“)。恩里科-普兰波利尼(Enrico Prampolini)等未来学家也是以马可尼的研究为基础(在马可尼纪念室中,他只因得到了这位科学家的赞扬而被回忆起: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Filiberto Menna 就指出,”建立在相对论和四维概念基础上的现代宇宙学,就像但丁的宇宙学建立在中世纪天文学基础上一样“。展览中不乏关于普兰波里尼和那些与他志同道合者的宇宙理想主义的精美展厅(这是展览中最成功的展厅之一),但也许人们低估了科学和马可尼的发现对他富有远见的绘画所做的贡献。Magister Art 的装置作品讲述了未来主义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本应向公众展示 ”人工智能和生成算法完全符合马里内蒂对未来的设想,他谈到了机器的人性化和人的机器化“(Simongini 在新闻发布会上如是说)。然而,我们并不清楚如何从一个发出彩色灯光(应该是 Boccioni 的 ”精神状态 ")并播放马里内蒂宣言的旋转木马中推断出这一切。
在新闻发布会上,未来主义的国际性也得到了强调,前部长桑吉利亚诺过去曾多次强调这一点,并在有机会时回顾了未来主义是如何成为一种前卫艺术并传播到世界各地的:由 Hultén 在 1986 年的展览上发起的国际未来主义调查,后来长期被忽视,Gnam 展 览也没有涉及(国际参展作品仅限于杜尚的《Nudo che scende le scale no. 杜尚的作品《Nudo che scende le scale no.1 》和施维特斯的拼贴画虽然重要,但参观者并不知晓它们出现的原因),就像未来派艺术家的国际关系主题一样,尽管去年在奥特罗的克勒勒-米勒博物馆举办的展览曾以这一主题为主题,但这次展览甚至没有触及这一主题。为了更深入地介绍未来主义,并让公众对其范围有一个真正的了解,如果能在最后一章中加入一个真正反映该运动国际性的部分,或许会更有帮助,该章将专门介绍那些参与未来主义运动的人。最后一章专门介绍那些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通过借鉴未来主义来发展自己的研究的艺术家(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几乎将自己置于连续性视角的艺术家也与那些对未来主义的态度是偶发性的艺术家混杂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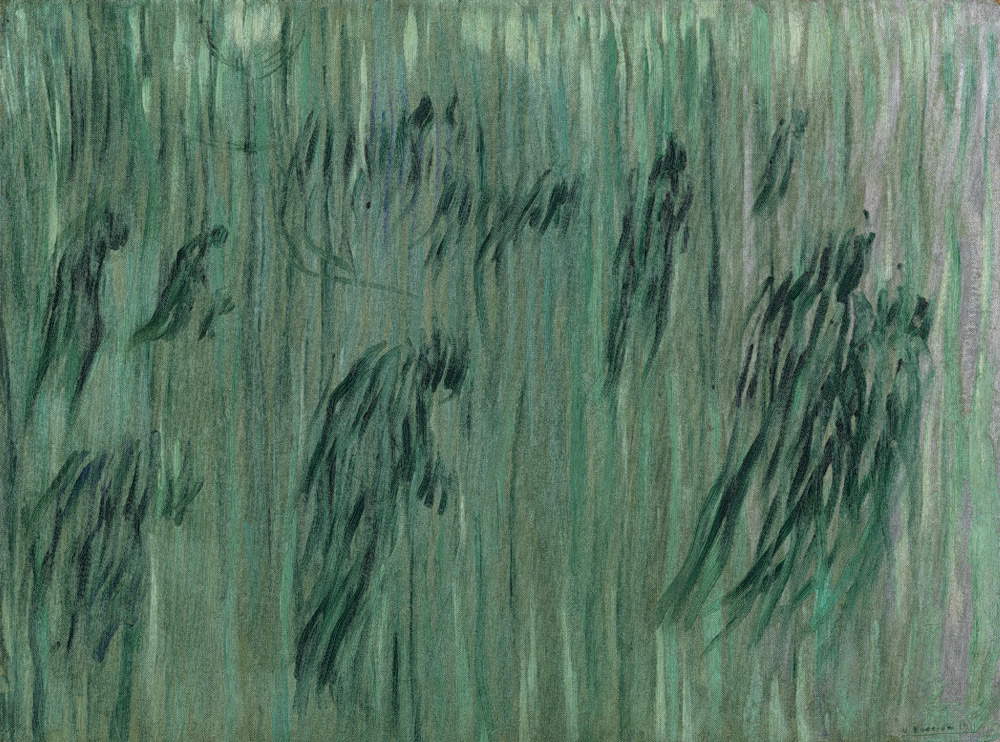












如果没有展览前夜的漫长期待,Il tempo del Futurismo 可能只是意大利博物馆几乎每年都会举办的众多未来主义展览之一。因此,它基本上是一个离散的、令人愉悦的、结构合理的展览,尤其是在第一展厅,它将一些分部主义杰作与博乔尼及其同伴的早期未来主义实验作品一起展出,向公众展示了艺术史并不是a watertight compartmentalised sequence as we are presented with in the manuals, an exhibition enlivened by a few flashes (Balla’sArc Lamp , Russolo’sRevolt , Balla’s triptych ofAffections and again hisChild running on the Balcony, Romani’sPortrait of Dina Galli , Boccioni’s triptych ofStates of的 三联画、Rougena Zatkova 的《Marinetti Soleil 》、Enrico Prampolini 的未来主义木偶(去年在雷焦艾米利亚的马格纳尼宫举办的木偶和牵线木偶展览就是以这些木偶拉开序幕的) 、Gerardo Dottori 的《Incendio città》) ,但都不是很大胆,非常循规蹈矩,缺乏国际气息。此外,展览缺乏深入的展板,无法让公众了解策展人的选择,还有一些作品似乎是在主要作品的中间位置出现的:例如,里贾纳的《Academico 》、杜德维尔的《Fioraio 》、尤利乌斯-埃沃拉的作品以及西罗尼的《芭蕾舞女 》都是如此。总之,对于那些已经看过近年来至少一次未来主义展览的人来说,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西蒙吉尼的评论在这种情况下值得一读,仅仅是因为有机会看到从藏品中提取的作品以及提到的少数几件国际借展作品。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从期望的角度出发,将其视为近十年来意大利最重要的展览之一,那么 "未来主义的时代 "就很难被视为一个里程碑。由于上述原因,由于不仅在展出作品方面,而且在涉及的主题方面都存在不足(例如,没有提及未来主义者、国际未来主义、未来主义者与 20 世纪初其他先锋派之间的关系、未来主义音乐、未来主义戏剧、帕拉迪尼和潘纳吉的机械主义的政治影响、无政府未来主义、未来主义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而且还与展览的力量部署有关。两年的规划、四千平方米的展览空间、150 万欧元的部级财政支出以及私人赞助)。
要知道,为了举办“未来主义的时代 ” 展览,必须拆除一半的博物馆,才能腾出 26 个展厅,让西蒙尼尼在这些展厅里展出他的作品,这些展厅占据了原 "时代 "的第三和第四展区:当然,这也无可厚非,只是在博物馆的另一半,只剩下克里斯蒂安娜-科卢(Cristiana Collu)那件令人质疑的装置作品的残片,那是博物馆参观者不得不忍受了七年之久的姗姗来迟的后现代作品的残骸。昨天,也就是展览向公众开放的第一天,除了 "未来的时代"(Il tempo del Futurismo )之外,只能参观旧布局的第二部分。换句话说,格南并没有费心为参观者在展厅内有序地介绍永久藏品: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前任馆长的创造性布置,说得难听点,只是截去了其中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参观博物馆的永久藏品几乎变得毫无意义。 难道格南想要建立一个真正具有马里内特风格和未来主义风格的博物馆吗? 在他们疑惑的时候,对永久藏品感兴趣的参观者将别无选择,只能等待 "秩序"的到来。

本文作者 : Federico Giannini
Nato a Massa nel 1986, si è laureato nel 2010 in Informatica Umanistica all’Università di Pisa. Nel 2009 ha iniziato a lavorare nel settore della comunicazione su web, con particolare riferimento alla comunicazione per i beni culturali. Nel 2017 ha fondato con Ilaria Baratta la rivista Finestre sull’Arte. Dalla fondazione è direttore responsabile della rivista. Nel 2025 ha scritto il libro Vero, Falso, Fake. Credenze, errori e falsità nel mondo dell'arte (Giunti editore). Collabora e ha collaborato con diverse riviste, tra cui Art e Dossier e Left, e per la televisione è stato autore del documentario Le mani dell’arte (Rai 5) ed è stato tra i presentatori del programma Dorian – L’arte non invecchia (Rai 5). Al suo attivo anche docenze in materia di giornalismo culturale all'Università di Genova e all'Ordine dei Giornalisti, inoltre partecipa regolarmente come relatore e moderatore su temi di arte e cultura a numerosi convegni (tra gli altri: Lu.Bec. Lucca Beni Culturali, Ro.Me Exhibition, Con-Vivere Festival, TTG Travel Experience).
免责声明:本篇意大利语原文的中文翻译由自动工具生成。 我们承诺会对所有文章进行审核,但无法保证完全避免因软件造成的翻译误差。 您可以点击 ITA 按钮查看原文。如发现任何错误,请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