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威尼斯双年展天真绘画倡议委员会 ”慷慨激昂地写信给卡洛-里帕-迪-梅纳(Carlo Ripa di Meana)以来,整整五十年过去了,当时他刚刚被任命为改革不久的双年展主席,要求双年展机构全面认可天真运动,或许可以在展览中举办一个 “天真 ”展,专门展出那些多年来被大多数评论家排斥、被贵族圈排斥、甚至经常被嘲弄,但却能够在世界上大放异彩的艺术家。1974年春:“天真 ”展专门为那些多年来被大多数评论家排斥、被贵族圈子排斥、甚至经常被嘲笑,但却能在市场上叱咤风云的 “天真者 ”举办,生动地体现了艺术史和品味史往往相去甚远的假设。那是 1974 年的春天:“我们确信,”委员会在给里帕-迪-梅纳和董事会的信中写道,“’新想象力’这一历史现象的重要性,你们不会不知道:一场被定义为天真艺术的运动的发展,从数量和质量上来说,都是越来越多的大众感性发展中的一个新事实,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所谓的新兴能量。我们面对的不再是学术之外的、原始的或流行的想象力[......]。我们面对的是一场永不停息、不断发展的运动,即使在当前民族文化的困难条件下,在与艺术和大众审美意识的复杂关系中。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准确而坚定的认识,我们要求你们具体地承认新的天真绘画具有充分的文化地位、职业尊严和艺术上应有的尊重,反对任何精英主义或从属的文化观念”。这封信的签署者没有想到,就在 2024 年的一个周年纪念日,来自世界各地的民间和野 蛮艺术家终于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展览上展出了他们的作品,他们梦寐以求的’边缘’ 艺术终于得到了机构的承认。尽管第 60 届双年展的策展人阿德里亚诺-佩德罗萨(Adriano Pedrosa)很难想象这是一种承认,他更愿意认为(尽管有些含蓄),在他的双年展上,土著、同性恋、外来者 艺术家的大量涌现,如果有的话,也是艺术史自然进程的平静结果。
从某种意义上说,佩德罗萨是对的,他在目录中发表的对朱丽叶塔-冈萨雷斯(Julieta González)的访谈中指出,对于欧洲或美国的参观者来说,要认出来自他所称的 “全球南部 ”的当代艺术家并不难,因为 “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和 21 世纪初以来,来自我们这个地区的当代艺术家获得了更高的知名度:即使不是所有艺术家,至少也有一些艺术家在博物馆、美术馆和双年展上巡回展出”。在意大利,也许我们的感受较少,因为我们的当代艺术博物馆通常遵循其他方向,但只要参观一下主要的博览会,就足以意识到许多画廊主提出的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艺术的吨位,这些画廊主不可避免地截获了一种品味和兴趣,至少二十年来,这种品味和兴趣越来越多地引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收藏家的胃口,在这个意义上,意大利人也不例外。因此,2024 年双年展的国际展览 "外国人无处不在--外国人无处不在"并没有揭示出任何值得注意的实质性新意(甚至连目录中的文章,除了克莱尔-方丹(Claire Fontaine)的唯一一篇未发表的文章外,都是 1998 年至 2023 年期间发表的文章的合集):如果说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一方面,双年展是对那些多年来一直在市场上出现的艺术家的官方认可,即使他们的报价很高,另一方面,双年展是对那些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讨论的一种放大,是向双年展的参观者展示那些在前几年由其他机构向欧洲和美国公众展示的艺术家的一种手段。在阿尔塞纳勒,克莱尔-方丹(Claire Fontaine)和银卡-肖尼巴雷(Yinka Shonibare)的作品拉开了双年展的序幕。但这一讨论可以扩展到展览中在世艺术家的绝对一致部分,甚至可能是大多数,他们在以白人和欧洲为中心的现金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无论他们是自学成才还是大众艺术家,或者相反,是具有传统、正规和学术背景的艺术家:Frieda Toranzo Jaeger(由 Barbara Weiss 画廊代理)、Emmi Whitehorse(Garth Greenan)、Greta Schödl (Labs 画廊)、Julia Isídrez (Gomide&Co)、Dana Awartani (Lisson)等等。就连原住民 Naminapu Maymuru-White,也就是展览说明中向我们介绍的 “伟大的 Yolnu 老人”,也将自己的兴趣委托给了整个亚太地区最顶尖的 画廊之一(澳大利亚的 Sullivan+Strumpf 画廊,巴塞尔艺术博览会的常客 之一)。
当然,同样的假设也适用于在 Giardini 中央展馆设立的展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除其他艺术家外,还有路易斯-弗拉蒂诺(Louis Fratino),他是目前最受市场追捧的艺术家之一(他与菲利波-德-皮西斯(Filippo de Pisis)进行了一场奇特而怪异的对话,原因是他们有共同的同性恋倾向,至少从标题中可以看出这一点),以及本地人凯-沃金斯蒂克(Kay Walkingstick),她在上一届 迈阿密巴塞尔艺术博览会上只 与她的画廊举办了一场展览 。而大多数非在世艺术家(占本届双年展参展艺术家的大多数)无论如何都已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伦敦泰特美术馆(Tate)以及许多主要的国际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过大型展览。如果我们想象佩德罗萨在亚马逊雨林中漫步,寻找亚诺玛米巫师的作品,以便向欧洲公众展示在我们的纬度上从未见过的图像,那就大失所望了:安德烈-塔尼基(André Taniki)和何塞卡-莫卡赫西(Joseca Mokahesi)的作品已经在我们大陆的博物馆巡回展出至少二十年了,卡地亚基金会于 2003 年率先举办了亚诺玛米展览。L’esprit de la forêt.简而言之,这些被遗弃的人,这些被制度边缘化的人在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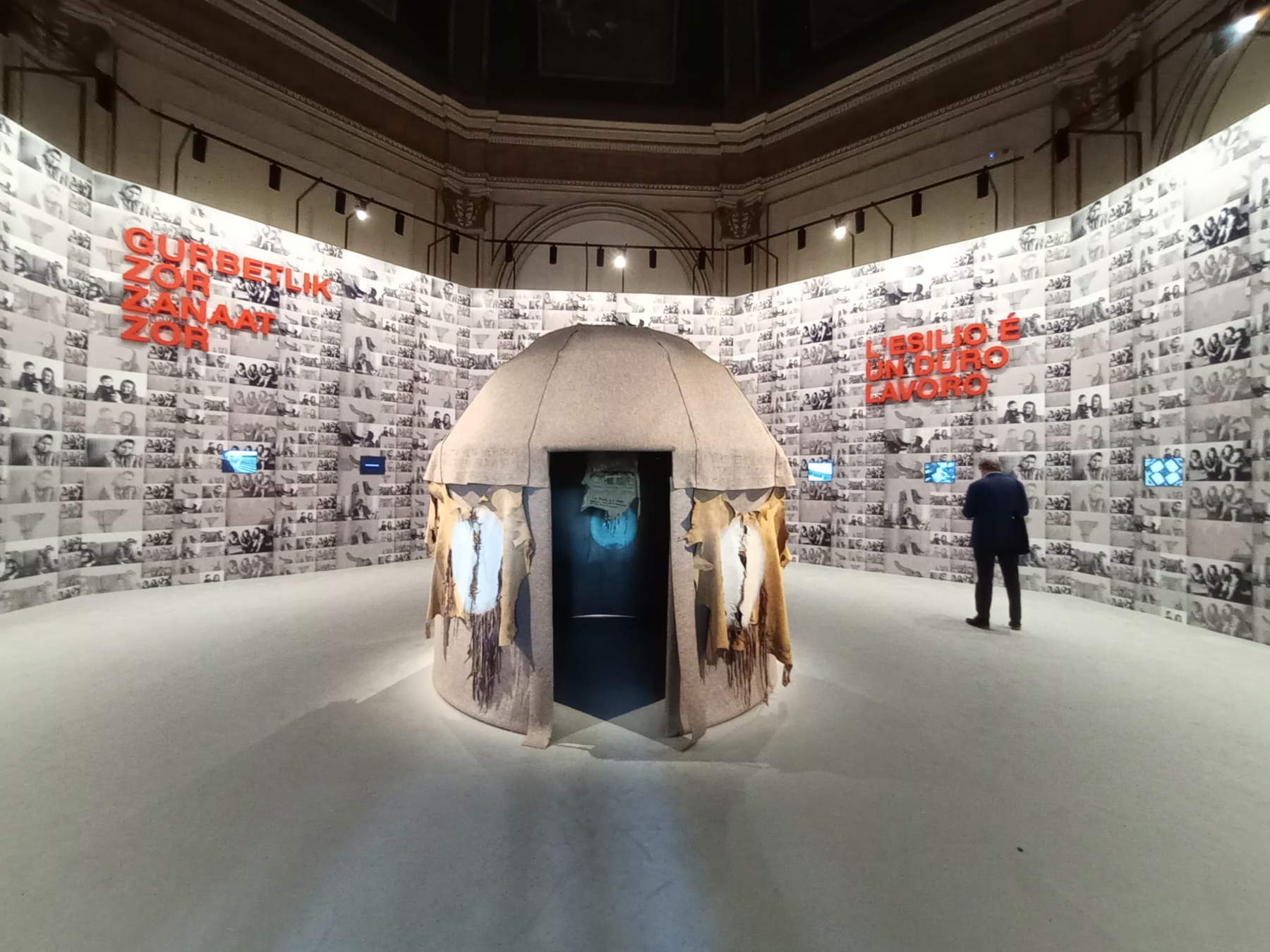

在上一届国际展览中,塞西莉亚-阿莱马尼(Cecilia Alemani)的《梦之奶》(Il latte dei sogni )就已经笼罩在殖民主义的阴影之下,而在本届国际展览中,这一阴影却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主题,因为本届国际展览旨在将非殖民化主题置于关注的中心。唯一没有回避这一主题的是蒂西奥-埃斯科瓦尔(Ticio Escobar),他在画册上发表的文章中强调,“大众 ”艺术家 “有权使用(主流文化干扰和干预的)所有渠道和机构,并将它们用作避难所、战壕,甚至作为潜在飞行的跑道”。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不能批评诉诸市场、争取更公平的价格和更大程度地承认大众创造性的决定”。这一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但它也提出了一系列同样重要的问题:一位与世界上最有权势的画廊之一签订合同,并将自己的作品带入当代艺术领域最制度化的环境中的艺术家,真的可以被说成是 “被排斥 ”的吗?那么,作为双年展基础的叙事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站得住脚?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认为一个过去几年来一直游走于巴黎、伦敦和上海之间的巫师的艺术是无意识的?难道没有利用这种流行的创造力达到与其预期效果完全相反的风险吗?萨满显然完全有权利诉诸欧洲和北美市场 ,以获得经济、文化和社会认可(事实上,许多外来者的梦想正是获得官方认可),但与此同时,公众也完全有权利质疑这一行动的效果,对一位多年来一直以西方市场衡量自己的艺术家的自发性、对他被排斥的真实程度、对他出现的真正原因提出一些问题:他在这里,是因为我们对他要说的话,甚至对他所在社区的状况真正感兴趣,还是因为我们把他作为一种好奇心 来展示,当我们厌倦了欣赏他那双从未接触过西方现代工具的手的技艺时,我们就会忘记他?早在 “天真派 ”爆发之时,吉安卡洛-马莫里就在他的一篇令人难忘的文章中指出,“天真派一旦被发现,就不可能长久地忽视他是天真派”,“今天,天真派几乎没有机会过秘密、真实和宁静的生活”: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当马莫里在《新闻报》上发表文章时,这一点是正确的,而在今天,在后全球化时代,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时代,在艺术界 观众习惯于旅行的今天,这一点更是正确的。
当然,佩德罗萨为他的展览(与以往的国际展览不同,这次展览的特点是更清晰、布局更简洁、更直接新鲜)所选择的几位艺术家或项目都能给公众带来惊喜,尤其是当人们不认识他们的时候:来自 Uitoto 民族的自学成才的画家 Santiago Yahuarcani 的远见卓识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作品以其亚马孙地区的缠绵森林、守护神和动物为背景,让人联想到 13 和 14 世纪我国教堂的普世判断。卡里马-阿什杜(Karimah Ashadu)在一段坦率的视频中讲述的尼日利亚摩托车出租车司机的故事令我们感动。土耳其艺术家居内斯-特尔科尔(Günes Terkol)的纺织品令人感动。她的纺织品将时事转变为一个几乎没有任何真实时间维度的故事,赋予了女性声音复调的生命,让我们立即产生共鸣。安哥拉人基卢安吉-基亚-亨达(Kiluanji Kia Henda)的整洁摄影作品有效而诗意地传达了特权和社会鸿沟的含义。曾在法恩扎生活和工作过一段时间的喀麦隆青年维克多-福措-尼耶(Victor Fotso Nyie)的金色陶瓷雕塑让人沉醉片刻。内达-圭迪(Nedda Guidi)是一位长期被边缘化的重要陶艺家,她之所以能参加此次展览,并不是因为她在 20 世纪下半叶的陶艺发展道路上发挥了先锋作用,而是因为她是一位"同性恋女性,一位坚定的女权主义者“。同样,我们也有机会领略马可-斯科蒂尼(Marco Scotini)的 ”不服从档案馆 "(Disobedience Archive )或巴勃罗-德拉诺(Pablo Delano)的 "旧殖民地博物馆"(Museum of the Old Colony )等项目的敏锐性。除了这些和其他一些尖锐的观点之外,《卫报》著名评论家乔纳森-琼斯(Jonathan Jones)八年前为在伦敦泰特美术馆举办的印度艺术家布本-卡哈尔(Bhupen Khakhar)展览(参加了本届双年展)所写的评论同样适用于佩德罗萨的双年展:"为什么泰特现代美术馆要展出一位老式的、二流的艺术家,他的艺术让人联想起它永远不会让其进门的那类英国画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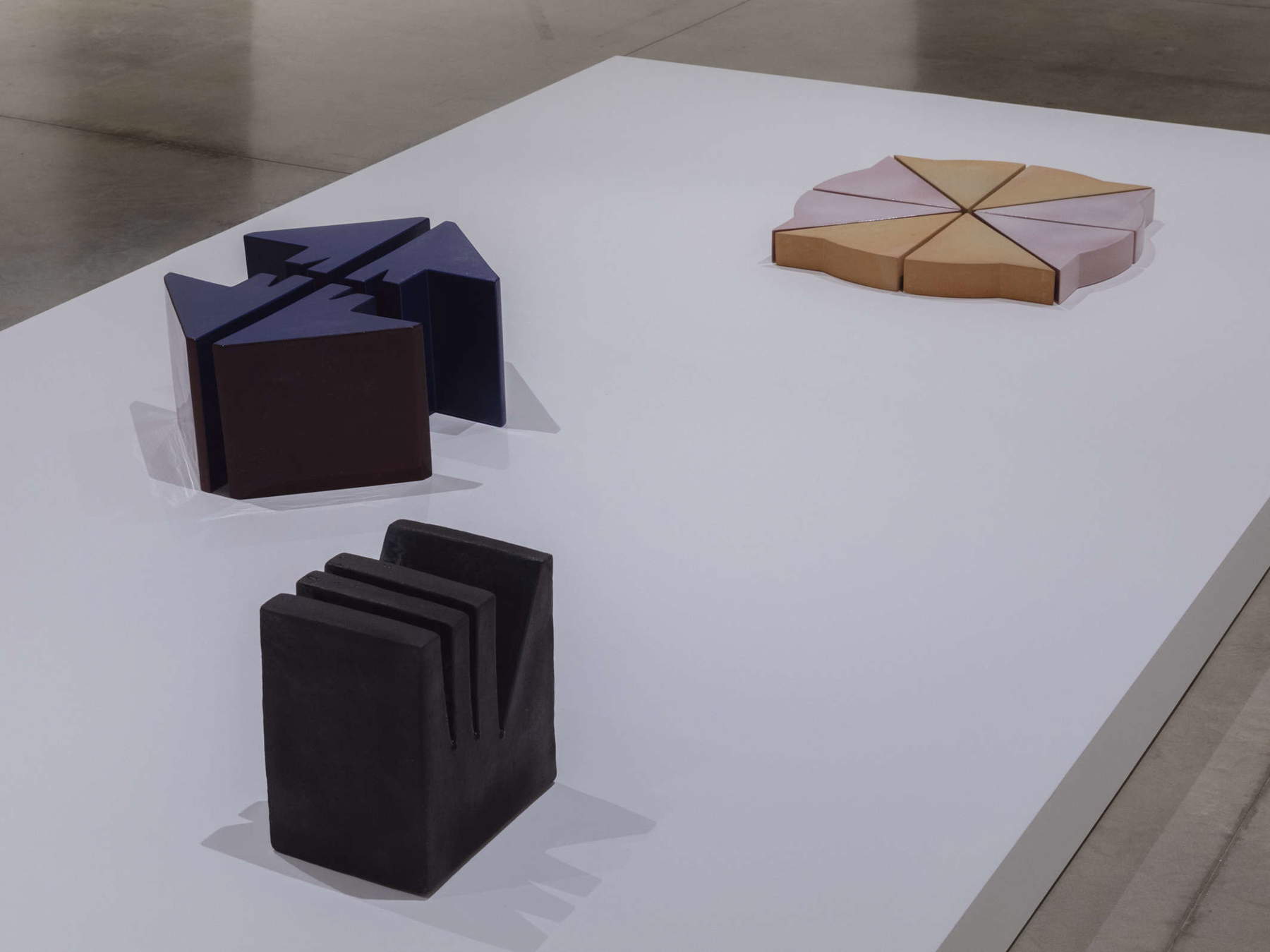

阿德里亚诺-佩德罗萨(Adriano Pedrosa)在他的双年展 中展示了大量外来者、民间和天真艺术作品,人们可以向他提出同样的问题:在亚马逊雨林中出生长大、自学成才的艺术家与战后艾米利亚地区众多从未进过博物馆或拿起过艺术史书籍的农民画家之间有什么区别?引用索菲奇的话说,一个土生土长的迪内人和一个从未见过教授胡子的亚平宁牧羊人有什么不同?我们的 Ghizzardi、我们的 Zinelli、我们的 Bolognesi 有什么特点不符合 Pedrosa 在其展览目录中对 "局外人 “的定义,即 ”发现自己处于艺术世界边缘的艺术家,就像自学成才者、民间艺术家或大众艺术家一样"?五十年前的委员会是何等的无奈:在双年展上被边缘化是没错,但前提是必须具有异国情调。将欧洲或北美的外来者 排除在外的唯一理由(展览中唯一的外来者 是奥地利人利奥波德-斯特罗布尔,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超出了意大利人、法国人或西班牙人最终会淡化我们对数百年来殖民主义的忏悔, 而我们却让世界其他地区遭受了殖民主义的蹂躏 ,除此之外,唯一的理由可能就是非正规艺术和民间艺术在其他大洲的艺术经济中所占的比重。
从这一假设出发,我们应该扪心自问,这是否是将威尼斯双年展纳入正在进行的文化非殖民化进程的最严肃、最正确的方式。换句话说: ,将被排斥者、原住民和同性恋者的单一集合体带到威尼斯,教条地割裂其他一切,只有极少数例外,这样做真的有用吗?可能没有,原因有几个。与此同时,即使本届双年展的艺术方向有着极好的意图,但它最终还是无意识地助长了一种对抗的态势,而这种态势甚至都不符合展览意图将其推向中心的被排斥者的利益(记得埃里科-马拉泰斯塔曾说过:“被压迫的群众[......]只有通过联合,通过与全世界所有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团结起来,才能解放自己”)。在其他领域和其他层面(因为我们都知道,视觉艺术已不再重要或不再有任何意义)所经历的这种动态,必然会导致(这一点可以从现实中看到)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反动谄媚的加强,这种谄媚从未停止过动摇 “世界的北方”--用本届双年展策展人常用的术语来说--。此外,当人们不是把艺术史理解为一个历史进程,而不是把它理解为一种对过去的清算、一种报复、一种对规则的攻击时,就很难不瞥见一种对立的逻辑。此外,这也没有什么用处,因为它有可能使双年展不再是当代世界的横断面,也许还带有某种确定未来方向的幌子,而是变成了一种被划分成若干房间的电影世界 ,变成了我们曾经称之为 “第三世界 ”的民间传说和手工艺品的汇编,其展览形式相当于摄影游猎。这一点得到了国内大批鱼子酱 爱好者的默许,他们在预展期间就已经沉浸在这个多姿多彩的展览中了,这里汇集了全球南方成千上万种奇妙的手工艺技术,他们还不忘在 Instagram 上晒出自己欣喜若狂的成果。在西方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再挖一条沟,难道没有风险吗?在威尼斯设立一个展厅,展出一系列蜡染、安第斯织物和萨满画,难道不会使这些艺术家面临助长对他们的成见的危险吗?或者使人们想要消除的边缘性更加明显?难道《外国人无处不在》所持的态度就没有可能像几个世纪前的人种学家一样,建立起他们的好奇心橱柜吗?顺便说一句,我们能不能最终摆脱 “流动艺术家仍应被视为’怪人’”的观念?
佩德罗萨双年展的局限性还体现在三个 “历史之核 ”上,这是对 20 世纪艺术史的三个小回顾,一个比另一个更令人尴尬,其设计具有 “当代之核 ”的所有缺陷。第一个 “历史之核”(如果想从 Arsenale 开始参观的话),即Italiani ovunque,我们引用目录中的话,“汇集了曾在国外旅行和生活,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以及美国和欧洲发展事业的意大利艺术家的作品”,“第一代和第二代意大利移民,他们在 20 世纪反过来成为世界南部和其他地区的外国人”。评选标准并不十分明确,因为除了确实离开意大利永久移居到其他地方的艺术家之外,还有像伽利略-奇尼(Galileo Chini)一样在泰国逗留了很长时间才完成一部作品的艺术家。他在泰国逗留的时间只够完成他受委托在那里完成的一件作品(奇怪的是,奇尼在当地的 唯一一件作品,即装饰贾尔迪尼中央展馆穹顶的壁画,却被蒙在鼓里:这是对入选艺术家的起码尊重)。然而,除了入选理由之外,“核心 ”不过是一种占据了整个房间的贴纸相册,是一群毫无关联的艺术家的无形组合,是一种将往往截然不同的经历汇聚在一起的模糊杂乱,甚至连美丽的甚至连美丽的布景(cavalete de cristal,1968 年由 Lina Bo Bardi 为圣保罗 MASP 设计的透明陈列架 ,即现在由佩德罗萨执掌的博物馆)也无法挽回这场糟糕展览的成果。
在 Giardini 的两个 “历史核心”(Historic Nuclei)中,抽象主义展区和肖像展区的情况也不尽如人意,这两个展区的目的都是为了观察 20 世纪早期运动的衰落,这些运动是由远离前卫艺术兴起的大陆的艺术家们创造的。这里也没有任何历史框架,只是想表明,20 世纪初,在欧洲和北美的推动中心产生了一些作品之后,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有一些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并在当地发展了来自其他中心的建议。这就是艺术史上的一贯情况:文艺复兴诞生于佛罗伦萨,但也有伦巴第文艺复兴、乌尔比诺文艺复兴、利古里亚文艺复兴等等,每个文艺复兴都有自己的气质和独创性。然而,任何严肃的艺术史家都不会想到在一个房间里举办展览,在那里博尔特拉菲奥(Boltraffio)、卡内瓦莱(Fra’ Carnevale)、卢多维科-布雷亚(Ludovico Brea)等人的作品散落在各个展厅,而不向参观者提供一些关于展出艺术家的传记以外的介绍。这就是参观者在花园的两个历史核心区漫步时所面临的情况:20世纪初非洲、拉美和亚洲艺术家的作品一览无余,没有标准,没有指南(只有简短的传记),没有明确的细分,在一片混乱中,即使是截然不同的背景之间也没有区别,真正原创的艺术家,如肖像部分的塔尔西拉-多-阿马拉尔(Tarsila do Amaral)或坎迪多-波尔蒂纳里(Candido Portinari),淹没在二三流画家之中,参观者最终可能会失去他们。因此,“历史核心 ”也是一个错失的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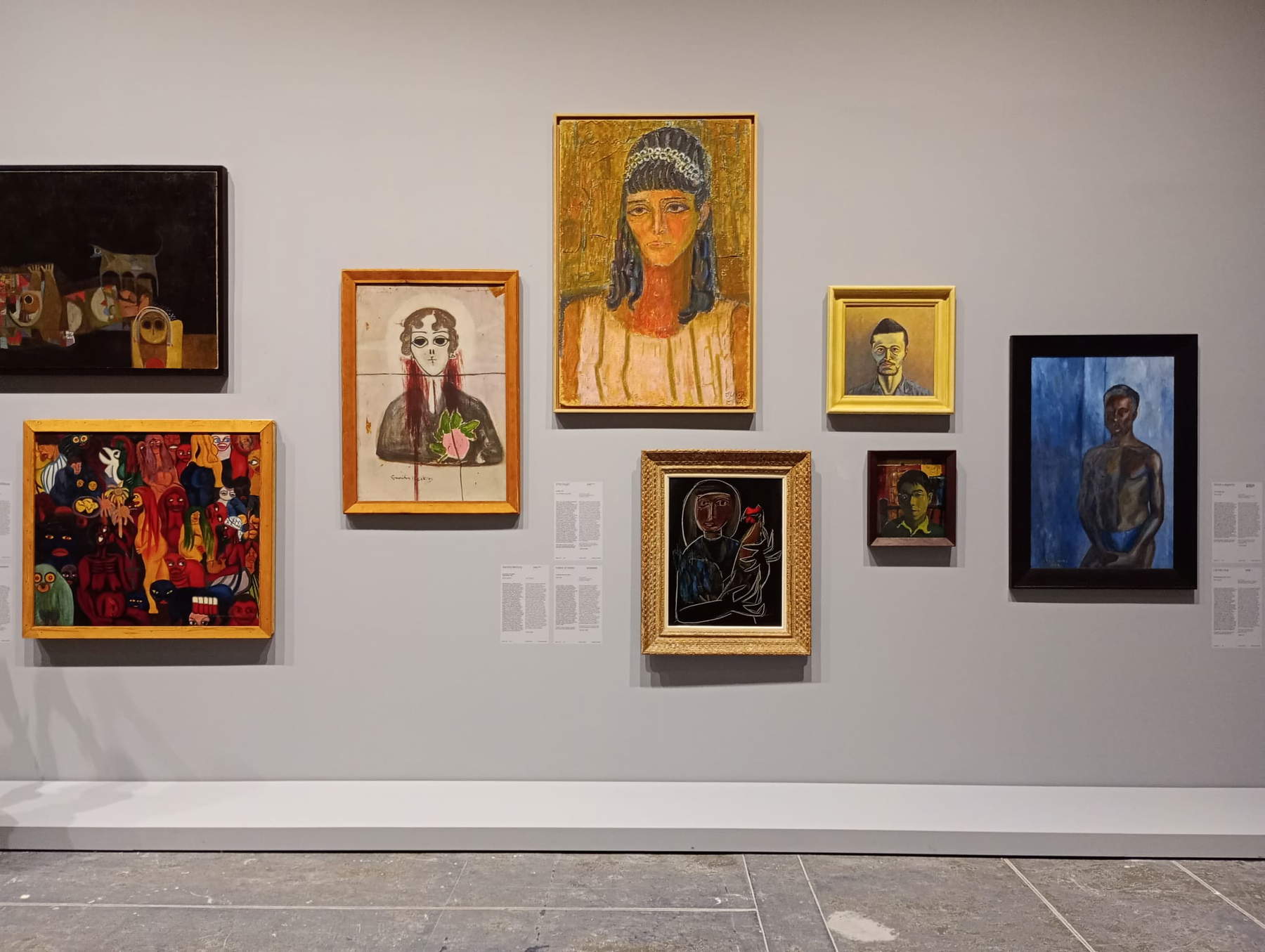
拉尔夫-鲁戈夫(Ralph Rugoff)策划的这届双年展可能不是历史上最好的一届,但却是最后一届,在这届双年展上,管理层将来自 “北方 ”和 “南方 ”的艺术家聚集在一起,没有贫民窟化,也没有摊牌的逻辑,将西方和南方的艺术产品置于同等地位。管理者将来自 “北方 ”和 “南方 ”的艺术家聚集在一起,没有贫民窟化,也没有摊牌的逻辑,将西方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艺术产品放在同等地位,其共同目标是提供一种世界观,并试图假设一条道路。虽然不能确定对未来的假设是否正确,也不能确定时代是否与策展人的想法相悖,但至少在过去,参观者有机会讨论一个方向。现在,要想在威尼斯找到一个有远见的艺术建议,就必须走出双年展,去看看皮埃尔-于盖在 Punta della Dogana 举办的声势浩大的展览,因为 "Stranieri ovunque - 外国人无处不在 "是一个无害、和蔼、公理化、不太精辟的展览,充其量只是一个总结。
前两届双年展更多的是为了迎合人们的口味,寻找对立面,对其他地方已经开始的讨论进行补充,甚至没有做出特别有趣的贡献。相反,2024 年双年展可能是一种倒退,因为今年的国际展览强加了一种非殖民化的理念,似乎几乎无视任何形式的对话。毕竟,佩德罗萨本人在接受朱丽叶塔-冈萨雷斯(Julieta González)的采访时曾表示,贾迪尼双年展的两个 “历史核心 ”存在的理由是 “挑战西方经典”。此外,非殖民化是对西方的挑战,这种想法在解决一个问题的假象下,最终会制造出其他问题:杰森-法拉戈在《纽约时报》上正确地指出了这种说法与普京的反殖民主义言论之间的联系,普京试图将他的俄罗斯宣传为非洲国家的朋友,同时又试图在历史之外将自己的帝国主义强加给乌克兰。那么,这就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文化非殖民化。
然而,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吗?当然有,而且可以在一些国家馆中找到(尽管没有多少国家馆超越了仅仅展示本国被排斥者的范围):例如,在法国馆中,朱利安-克鲁泽(Julien Creuzet)通过一件充满诗意的作品表明,非殖民化进程应被想象为一个不仅重新思考我们的政治结构,而且重新思考我们在世界上的定位的时刻。那么,非殖民化就是重组,而不是挑战或清算。否则,我们就会满足于一些异国情调的幼稚想法,继续认为我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五十年前的委员会可能会欢欣鼓舞。

本文作者 : Federico Giannini
Nato a Massa nel 1986, si è laureato nel 2010 in Informatica Umanistica all’Università di Pisa. Nel 2009 ha iniziato a lavorare nel settore della comunicazione su web, con particolare riferimento alla comunicazione per i beni culturali. Nel 2017 ha fondato con Ilaria Baratta la rivista Finestre sull’Arte. Dalla fondazione è direttore responsabile della rivista. Nel 2025 ha scritto il libro Vero, Falso, Fake. Credenze, errori e falsità nel mondo dell'arte (Giunti editore). Collabora e ha collaborato con diverse riviste, tra cui Art e Dossier e Left, e per la televisione è stato autore del documentario Le mani dell’arte (Rai 5) ed è stato tra i presentatori del programma Dorian – L’arte non invecchia (Rai 5). Al suo attivo anche docenze in materia di giornalismo culturale all'Università di Genova e all'Ordine dei Giornalisti, inoltre partecipa regolarmente come relatore e moderatore su temi di arte e cultura a numerosi convegni (tra gli altri: Lu.Bec. Lucca Beni Culturali, Ro.Me Exhibition, Con-Vivere Festival, TTG Travel Experience).
免责声明:本篇意大利语原文的中文翻译由自动工具生成。 我们承诺会对所有文章进行审核,但无法保证完全避免因软件造成的翻译误差。 您可以点击 ITA 按钮查看原文。如发现任何错误,请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