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 6 月 26 日在罗马逝世的 99 岁高龄的伟大作家拉法埃莱-拉-卡普里亚,我们刊登了 2008 年布鲁诺-赞纳尔迪(Bruno Zanardi)对拉-卡普里亚的访谈,主题是拉-卡普里亚和乔瓦尼-乌尔巴尼之间的长期友谊。 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影响意大利文化遗产的各种事件的背景下,我们看到了两位伟大人物和知识分子的重要形象,他们既现代又有远见。
我在拉斐尔-拉卡普里亚位于多利亚宫的迷宫般的公寓里见到了他,在这个温暖的十月,从他的窗户看出去,罗马显得更加甜美和慵懒。我们开始怀着深情和忧郁回忆乔瓦尼-乌尔巴尼。但很快,谈话就变成了意见交锋。这是一场亲密但温和的对峙,就像拉斐尔经常与乌尔巴尼进行的亲切的智力挑战一样。“1994年6月10日上午,拉斐尔在乌尔巴尼的葬礼上,在圣贾科莫教堂(San Giacomo degli Incurabili)发表了凄厉的演说。正是拉斐尔陪着乌尔巴尼的遗体前往火葬场,”当他走出火葬场(......)时,他看到一股浓浓的油烟从高高的烟囱里升起,散向湛蓝的天空。’我想,那烟是约翰要走了’"。他在《L’estro quotidiano》中这样描述道,这部小说主要是 “为了纪念乔瓦尼 ”而写的。

BZ.您第一次见到乌尔巴尼是什么时候?
RLC.1957 年春天,在罗马。作为意大利人,我们应邀参加了哈佛大学举办的一次关于政治、经济和艺术的国际研讨会。他想见见我,因为这些研讨会持续了几个月,所以我们应该在一起很长时间了。我们约好在拉伊见面,当时我正在那里工作。我在通往办公室的楼梯口等他。他跳过我们之间的最后几级台阶,一起向我伸出手,表示友好。就在这两个举手投足间,一个符合我审美标准的男人出现在我面前。他身材高大、修长、慵懒,面容和蔼可亲、低调而快乐,穿着一套浅色缎面西服,非常优雅,显然是由一位出色的裁缝裁剪的:在那个年代,作为一个优秀的那不勒斯人,我非常关注西服和裁缝。在我看来,这个陌生人马上就会成为我的朋友。就像康拉德笔下的吉姆勋爵,“我们自己人”。
当时我还无法想象吉姆 “对无法忍受的事物的敏锐感知 ”与乌尔巴尼是如何相同的。他还不知道,《吉姆勋爵》是他的著作之一:当他因为一个失宠的外科医生而死在罗马疗养院时,他带走的就是这本著作。那本历史悠久的邦皮亚尼版的康拉德作品,浅蓝色的封面,你自己保存在他的记忆中,他把它打开放在床头柜上,上面有一幅吉姆的简短画像,他在画像下划了横线,显然他认出了自己:“那些具有杰出品质的人之一,没有愚蠢到孵化成功,他们往往以耻辱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但究竟是谁选择了你参加哈佛研讨会?
这我就不知道了。是美国人根据他们自己的考虑做出的决定,我认为其中最主要的考虑是,乔瓦尼和我属于意大利知识分子中亲西方的一方。这是一个非常精确的自由主义社会,围绕着马里奥-帕农齐奥(Mario Panunzio)的《世界报》(Il Mondo)或维托里奥-卡勒夫(Vittorio Calef)的《国体报》(Il Punto),乔瓦尼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半期到下一个十年初为这两份刊物写了大量文章,其中关于后者的多于关于前者的。贝内代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的阴影和加埃塔诺-萨尔维米尼(Gaetano Salvemini)的公民承诺仍然笼罩着这个知识分子社会,其中包括埃尼奥-弗莱亚诺(Ennio Flaiano)、阿尔贝托-莫拉维亚(Alberto Moravia)、艾尔莎-莫兰特(Elsa Morante)、乔治-巴萨尼(Giorgio Bassani)、桑德罗-德费奥(Sandro De Feo)、文森佐-塔拉里科(Vincenzo Talarico)、米诺-马卡里(Mino Maccari)、乔瓦尼-鲁索(Giovanni Russo)、保罗-米兰(Paolo Milano)等人。我知道是谁提议我们参加这次研讨会的。乔瓦尼是切萨雷-布兰迪(Cesare Brandi)推荐的,我是埃内斯托-罗西(ErnestoRossi)推荐的,他是《世界报》(Il Mondo)的支柱,也是《Settimo non rubare》或《Ipadroni del vapore》等名著的作者。
布兰迪向哈佛大学推荐了乌尔巴尼。那时,他们之间还没有出现从未公开承认过的对彼此理论立场的不信任。仅就修复而言,布兰迪将其思想集中于个别作品的美学修复。乌尔巴尼则将布兰迪的立场历史化,探讨了过去艺术的命运及其与环境的关系这一根本问题,而这在意大利是不可分割的。
据我所知,乔瓦尼和布兰迪之间唯一的裂痕并不是因为思想立场的不同,而是因为世俗性质的小分歧,但这种分歧很快就被无关紧要的事情所掩盖。他们之间的感情和尊敬使他们终生难忘。然而,布兰迪在谈话和游记中平易近人、魅力十足,但至少在我看来,他的艺术评论却变得抽象和理论化了。
乌尔巴尼微笑着告诉我,如果乔治-曼加内利(Giorgio Manganelli)将布兰迪的两个哲学新词 “l’attante ”和 “l’astanza ”转化为 “在艺术中哭泣的 attante ”和 “在艺术中哭泣的 l’astanza”:“在绝望中哭泣的attante”。1957 年春末,您去了美国。
我们是乘 "独立号 "轮船去的,因为那是哈佛付给我们的旅费。在到达美国的七天时间里,我们巩固了友谊,这段友谊后来让我和约翰形影不离。那是一次美好的旅行非常有趣我们遇到了两个美国女孩,我们用笑话、十字架和笑声向她们求爱。那是晚年生活的充实,也是对我们在意大利所经历的个人困境的遗忘。
伤逝“的 ”美好日子 "的黄昏?
也许是希望另一个 “美好的一天 ”能在美国开始。自由的国度。那是一片遥远的土地,混合着魅力、爵士乐、黑帮以及我们从电影和小说中想象到的其他一切。法西斯主义阻止我们阅读的那些作家,福特-马多克斯-福特(Ford Madox Ford)推崇的作家,例如海明威(Hemingway),以及我们在维托里尼的《美国人》(Americana)中领略到的其他作家:斯科特-菲茨杰拉德(Scott Fitzgerald)、萨洛扬(Saroyan)、斯坦贝克(Steinbeck)或约翰-方特(John Fante),还有更年轻的作家,例如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他在1952年至1953年间来罗马拍摄电影,并在我附近的马古塔街(via Margutta)住过几个月。马古塔街与乔瓦尼最后的家是同一条街。
在看过和读过乌尔巴尼的电影和小说四十年后,我仍然对它们津津乐道。歹徒》为海明威非常短小、神秘而优美的短篇小说《杀手》扩展和创造了一个结局。或者《大沉睡》,这部钱德勒小说的电影译本,由亨弗莱-鲍嘉和劳伦-白考尔主演。他告诉我,这部电影是他在卡普里看的,那是一个夏天的傍晚,在一家为休养的美国士兵开设的露天电影院里。在哈佛大学的国际研讨会上,您直接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从导演亨利-基辛格到李-斯特拉斯伯格、艾伦-泰特,甚至约瑟夫-麦卡锡,您写道,乌尔巴尼 “用他的风度迷住了他”。
我们在纽约停留过。我朋友比尔-韦弗(Bill Weaver)的一个朋友把他的公寓给了我们。那是一个特别炎热的夏天。酷热难耐。和约翰一起,我们在摩天大楼之间的街道上闲逛,摩天大楼的玻璃幕墙闪闪发光。日复一日,我们发现了这座奇妙城市的博物馆、建筑和公园,当时,这座城市在知识方面受到了狂热和活力的支配,人们正在为具象艺术寻找新的视野:行动绘画,但当时已经是新达达主义的时代,接近波普艺术。


回到意大利后,1961 年,您凭借《伤逝》(Ferito a morte)获得了 Strega 奖,正如您在《L’estro quotidiano》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当胜利的选票到手时,“是乔瓦尼像对待冠军一样将我托起”。三年前的1958年,乌尔巴尼担任新成立的斯波莱托艺术节的艺术总监,在那里他组织了一个开创性的展览--"意大利和美国青年艺术家第一选展"(Prima Selezione di Giovani Artisti Italiani e Americani)--尽管如此,他在 “Il Punto ”中表达的对当代艺术的困惑仍然得到了证实。劳申伯格的作品《床》(Bed)被他排除在展览之外,他认为这不是一件艺术品,而是一件无用的噱头:垂直放置一张床,并以波洛克(Pollock)的 "滴水"方式,凭感觉在床上泼洒色彩。必须指出的是,这一决定也没有引起丑闻。直到多年后,评论家们,也就是市场,才把那张毫无用处的立式床变成了当代艺术的杰作,如今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隆重展出。这一事件也揭示了乌尔巴尼被误解的问题:过去的艺术和今天的艺术是否具有相同的真理价值。他的思考首先来自海德格尔的思想,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他就开始沉思海德格尔的文章。由于他不懂德语,而且当时只有《存在与时间》,意大利语版本也不多,所以他只读了法文译本。
然而,我从未读过海德格尔。约翰的问题在于他对抽象概念、理论和高深思想的无敌吸引力。黑格尔也是他的宠儿。他经常凭记忆引用《美学》中的段落,试图在我们关于艺术和文学的有趣争吵中让我闭嘴。事实上,乔瓦尼对智慧的尊重是不相称的。而这也阻挡了他。这成了他的智力监狱。这让他写出了才华横溢、高深莫测的作品,但却不如他自己。我确信乔万尼的内心深处还有另一个乔万尼,他和我一样用常识思考问题,但他认为常识不如他正在进行的研究。在我看来,他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他对自己选择的知识模式缺乏安全感,这阻碍了他的写作。不过,这只是我的观点。也许对你来说,情况并非如此。
相反,我认为你是对的。但事实是,他在 1960 年发表的题为《偶然性在当今艺术中的作用》的演讲,是迄今为止对当代艺术问题最深刻、最有说服力、最精炼的沉思之一。乔治-阿甘本称之为 “小杰作”。
我记得他在罗马国家现代艺术馆发表了演讲。我能说什么呢?关于当代艺术中存在随机性这一事实,乔瓦尼很可能一语中的。但这仍然是一场赌博。有趣的是,他在这场赌博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理论。在我的《瓶中蝇》中,我也对当今的艺术提出了一些冒险的观点。然而,我并没有将其作为绝对的判断。这是我与当代艺术的关系,是个人的事实。
这也许是个人的事实,但在你的那本理性主义小册子中,你支持乌尔巴尼也非常坚持的一个论点,即当今的艺术不是艺术,而是 “对艺术的批判性反思”,也就是艺术批评。谈到皮耶罗-曼佐尼(Piero Manzoni)嘲讽的《艺术家的狗屎》(Merda d’artista)时,您写道:“这些背离常识的行为与其说是与作品有关,不如说是与脆弱易逝的概念有关,而当概念消亡时,作品依然存在”。因此,我的结论是,你只剩下一罐狗屎。
当代艺术是对艺术的模仿。它以概念为基础,这些概念只要还活着,就会自我维持:就好像在那一刻,围绕着作品产生了一种信仰。然而,或多或少,这些概念很快就会消亡,最终,所有这些作品又回到了平庸地只代表自己的物品上。我相信这也是乔瓦尼决定不在斯波莱托展出劳申伯格的《床》的考虑因素。
乌尔巴尼总是对当代艺术进行反潮流的干预,人们对他的评价如何?例如,他独自批评了他的朋友乔瓦尼-卡兰敦特(Giovanni Carandente)于 1962 年在斯波莱托为艺术节举办的 “城市中的当代雕塑展”。作为首次举办的此类展览,该展览立即获得了一致认可。乌尔巴尼则认为,这预示着一种危险,即在意识形态和短暂的 “新 ”的名义下,城市千年来形成的历史和环境价值将被抹去。他还预示了这样一种危险:如果不首先对过去在我们世界中存在的意义进行深思熟虑的反省,这种危险就会发生。因此,他几乎在半个世纪前就预见到了今天正在发生的事情,不仅在我们这里,而且在全世界:一种日益平庸和丑陋的新事物的 “多米诺骨牌效应”,它驱赶着古老的形式。
关于斯波莱托,我并不记得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尽管你所说的不幸似乎非常正确。至于乔瓦尼关于当代艺术的文章,你必须考虑到,在那些年里,如果你不谈论 “艺术之死”,你就不时髦。那是永久前卫的年代,每个人都成立了 “团体”,无论他们对新的艺术运动是倾向还是厌恶。在这种情况下,乔瓦尼的文章给人的印象是与这些观点不谋而合。不过,他是在以一种更复杂的方式谈论它们。一种为少数人准备的复杂性。然而,我相信,乔瓦尼对当今艺术(正如他所说的 “人人都能创造的艺术”)的意义的怀疑中,蕴含着某种神秘的东西。谁相信上帝,谁就没有找到上帝。谁感到上帝不存在,谁就相信上帝。在我看来,这是约翰艺术思想的核心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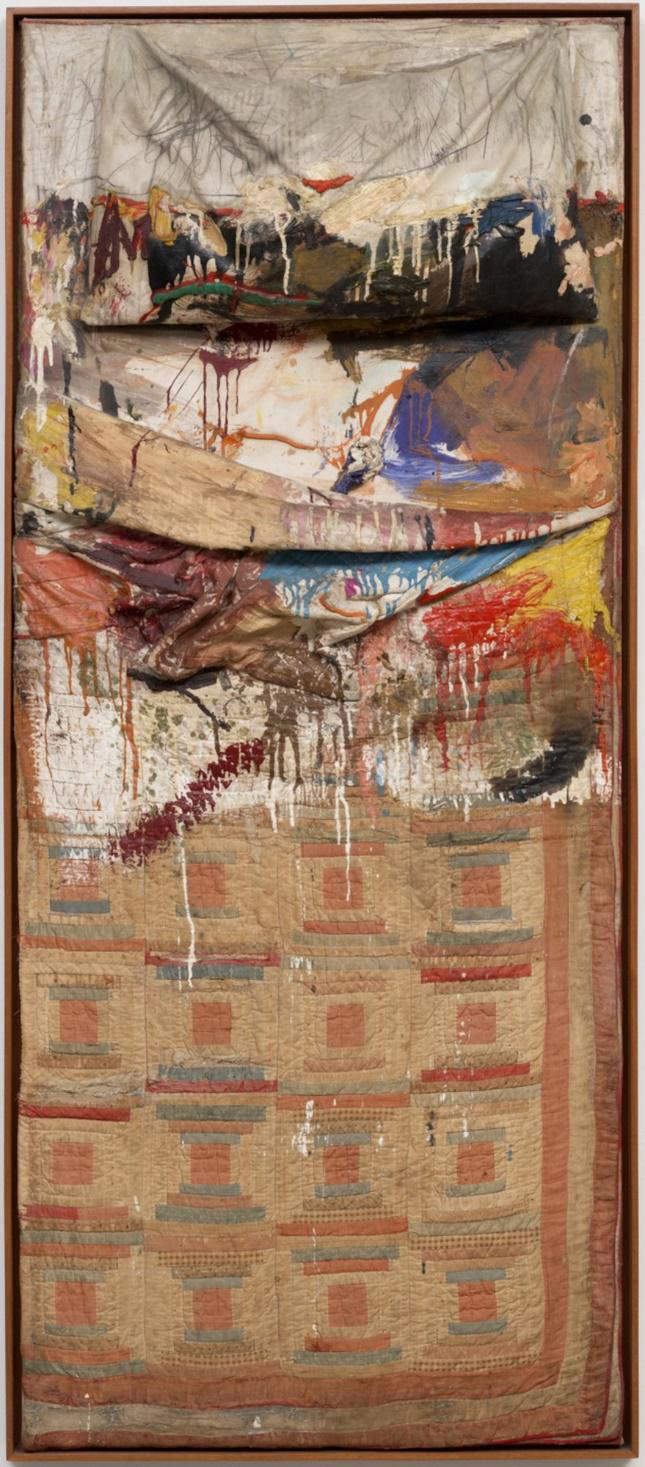


但乌尔巴尼从未谈论过艺术的死亡,对他而言,艺术与海德格尔一样,是 “真理的呈现”。相反,他和海德格尔一样想知道,作为当代艺术的审美意义上的 “生活体验 ”是否是 “艺术正在消亡的因素”。正如其日益歇斯底里地坚持--在市场和评论家的帮助和怂恿下--成为对自身的批判,沉溺于重复和过度的’挑衅’所证明的那样。无用的艺术。纯粹的装饰。
当然,当代艺术的真理并非里亚斯青铜器或西斯廷教堂的永恒真理。它是一种易逝的真理。是当下的真理。但主旨是存在的,否则就不会有艺术。我们又回到了约翰对抽象思维的无敌吸引力。这使得他的文字总是非常复杂。但我说,他的写作也是内卷化的。之所以说他的写作是不连贯的,是因为他有时会被时间和思想所纠缠,就像猫在毛线团里一样。在我看来,他写作时就有这种缺陷。但她不愿意听我说这些,她把自己思想上的困难归咎于别人。他对我也是这样。当我们谈论哲学时,他总是面带微笑,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对于我,他认为可以把我归为从真实的角度来看有趣的人,就像一个告诉你 “国王赤身裸体 ”的人一样有趣。这是我们之间的一个挑战,一个充满感情和微笑的挑战,在这个挑战中,他扮演堂吉诃德,而我扮演桑丘-潘沙。
乌尔巴尼的文字也许不仅仅是无意识的,而是有要求的。它们要求阅读者对自己的公民义务承担起强烈的责任,要求阅读者认真准备好应对命运要求我们面对的问题。然而,我们将过多的注意力放在了乌尔巴尼作为当今艺术批评家的身上,也就是说,乌尔巴尼在保护过去艺术的道路上所走过的仅仅是一个阶段。简单地说,这条道路可以分为三个步骤。
乔瓦尼是一个非常苛刻的人,这是千真万确的。他做任何事情都非常认真和严谨。他要求别人也同样严格,至少他期望如此。但我打断你了你刚才跟我说了乔瓦尼在保护过去艺术的过程中所经历的三个步骤你认为它们是什么?
第一个步骤是从他 1945 年加入 Icr 到你去美国的这段时间。在这十来年中,他注意到了修复干预的重大不稳定性--批判性的和保守的--首先是Icr进行的干预,当时是最高级别的。以至于在我认为是他的另一部 “短篇杰作 ”的 1967 年文章《修复与艺术史》(Il restauro e la storia dell’arte)中,他问道:“那么,我们是否还可以说,我们并没有像以往那样进行修复:即改变或篡改?第二段大致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到随后的十年,与他对当今艺术与过去艺术的意义的深思不谋而合。结论是,前者与后者没有真正的连续性。因此,保护过去的艺术是当今人类的命运。第三步,也是最后一步,是在 1966 年佛罗伦萨洪灾之后。在这场严重的灾难之后,他为保护与环境相关的历史、艺术和文化遗产制定了一个宏伟的组织设计。一方面,他发明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技术--显然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技术--他将其命名为 ”程序化保护“。另一方面,他建立了 ”文化生态学“,承认艺术遗产是 ”人类环境的组成部分,与自然环境组成部分之间的生态平衡一样,是物种福祉所必需的"。
乔瓦尼确实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他的理论非常精炼和复杂,在解决技术和组织问题时又无限务实和准时。此外,正如我在《L’estro quotidiano》一书中所写的那样,"乔瓦尼的真正独创性在于他的矛盾,这些矛盾有时是站不住脚的,常常是互不相容的,但却总是不可抗拒的,他从未因一种存在的不耐烦而将自己封闭在一个明确的形象中。
我不会说乌尔巴尼的这两张面孔之间存在任何矛盾。特质 d’union "是坚信思想的阐释总是要有具体的应用指示,正如他所写的那样,这对于 “将过去的物质融入人的成长 ”至关重要。诚然,乌尔巴尼的形象在很多方面都与容格笔下的 “无政府主义者 ”相似,即 “即使在军队行列中也要进行自己的战争 ”的人。只是他的战争比他所面对的军队的力量要强得多。监管者,他们仍然把保护理解为十九世纪的权力行使,凭借的是官僚的能力,因此是禁止和许可的事务,而绝不是目的,因此是理性和连贯的行动。
让乔瓦尼为保护我们的艺术遗产所做的工作付诸东流确实是一种罪过。他如此认真地为之准备。让他自生自灭,甚至让他决定摔门而去。1983 年,他提前辞去了 Icr 院长的职务。乔瓦尼坚定地相信他以绝对的热情为之服务的国家。但国家也背叛了他。对他来说,祖国就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一系列艺术作品。因此,他感到捍卫祖国的义务和光荣。这就是他来到修复研究所的初衷。但负责管理我们这个国家的机构从未认识到他的工作的重要性和实用性。他的奉献精神乔瓦尼的故事是一个知识和道德多样性的故事。他的同事们认为这是一种危险。
然而,我认为也有非常具体的经济利益原因。乌尔巴尼将保护艺术遗产与保护环境融为一体的想法不可避免地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我国发生的自由领土侵略相冲突。我认为这是乌尔巴尼反对这一政策的决定性原因,事实上,乌尔巴尼始终支持建筑投机,不管是哪一方。
我在 1963 年编剧了弗朗切斯科-罗西的《城市之手》,因此我熟悉我国城市灾难的逻辑。事实上,在当时,由于我们的努力,一切似乎都有可能改变。正如我所写的那样,我们真的是’历史的笑柄’,尽管是在另一种背景下。约翰也是如此,他认为在我们的国家,有一些人真正关心艺术遗产和景观的保管和保护。
事实上,文化部门的落后与维护投机利益是背道而驰的。1976 年,针对 “翁布里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计划”(乌尔巴尼最信任的与环境有关的艺术遗产保护组织项目)的激烈争论就源于此。该计划是乌尔巴尼请求埃尼公司(Eni)的工业科技研究提供帮助而起草的。乌尔巴尼的所有同僚和许多大学教授团结一致,共同反对该行业的现代化。乌尔巴尼让一个拥有充足的技术和企业能力以及真正的运营手段的工业结构,也就是埃尼公司,参与进来,从而对官僚国家主义的不动产主义构成了严重威胁,而这种不动产主义在意大利一直都是赢家。事实上,主管和教授们赢了。而教育部门则完全静止不动。
这是一次愚蠢而暴力的侵略,乔瓦尼深受其害。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在那些年里,那些能够理解和欣赏乔万尼所做工作的伟大艺术史学家们依然健在。布兰迪当然能够理解乔瓦尼的计划。阿甘和泽里也是如此。他们都能理解乔瓦尼的工作对于保护过去艺术的价值和作用。他们为什么不为他辩护呢?
正是因为他们无法理解这些项目。也许只有布兰迪真正了解乌尔巴尼的工作。而阿尔甘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他根本就没有看过翁布里亚 “计划”,但他作为一个有权势的人,知道艺术史学家协会(他自己的协会)会因该计划的实施而大打折扣,因此他宣布反对翁布里亚 “计划”。此外,阿尔甘和乌尔巴尼之间存在着一种遥远而不可战胜的敌意,这首先与性格有关,但也可能源于他们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期间对当代艺术所持的不同立场。阿尔冈是共产主义者,意识形态色彩浓厚,支持商业化。乌尔巴尼是自由主义者,独立自主,确信画布上随意绘制的楣画、头顶床单的纸糊大象或烧焦的塑料片不可能具有任何真正而持久的价值:首先是真实性,同时也是经济性。相反,泽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向我承认了他的错误,即低估了乌尔巴尼思想的深度。
难道说乔瓦尼没有受到任何人的维护吗?甚至是他的主人?甚至布兰迪也没有,布兰迪在很多方面都提拔了他,但在他的创造力和公民激情的这个如此重要的方面却没有?说这些话是为了纪念乔瓦尼吗?
最后,我想回到您的《伤逝》。即使是乌尔巴尼,即使是他 “美丽的一天 ”永远的终结,人们是否可以说:“如果你愿意,可以把它写成一个谜,但不要写成戏剧”?
不幸的是,我认为乔万尼的 “美丽一天 ”不可能 “成为一个谜,而不是一出戏剧”。和吉姆勋爵一样,约翰一生都背负着需要赎罪的污点。这个污点是一个有荣誉感的人的心理状态,他首先是一个有荣誉感的人,他时不时地会为他幼年夭折的独子感到悲痛,为他的势利眼感到悲痛,为他孜孜不倦、充满激情的工作的失败感到悲痛,天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这是她无意识中不可磨灭的污点和阴影。但你知道解释生活有多难吗?要解释无意义地浪费了约翰这个了不起的人有多难?“Dón Gió/vanni/ Búrlador/, maître à pensèr/ e grànd charmèur...’”,这是我过去经常唱给他听的一首童谣,是我为他编的,有时还哼给他听,作为《卡门》中 “Toreador ”埃斯卡米洛的咏叹调的笑话......
(2008年10月)
免责声明:本篇意大利语原文的中文翻译由自动工具生成。 我们承诺会对所有文章进行审核,但无法保证完全避免因软件造成的翻译误差。 您可以点击 ITA 按钮查看原文。如发现任何错误,请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