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清楚地知道,尼采提出的 "平等永恒回归 "理论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哲学论述,更不是一个潜在的科学假说,而是一个黑暗的预言。但是,正如乌托邦小说向我们展示另一种可怕的现实,从而让我们反思我们的社会一样,宇宙循环往复地重生和消亡这一概念也表明了我们对存在的某些理解。例如,它让我们思考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某件事情发生过一次,然后消散于无形,那么它几乎就像从未发生过一样。如果我们把它想象成孤立于存在所构成的事件海洋中,它实际上是相当微不足道的。另一方面,那些死而不僵的事物,尽管迟早会回到阴影中,但却具有更明确的存在意义。在艺术界,绘画无疑扮演着这样的角色。
它也许是最早诞生的创造性表现形式(与洞穴艺术一起),也肯定是最后消亡的。如果说从战后到 1910 年代,在意大利(和西方其他国家一样),除了 "跨 文艺复兴时期"(Transavantgarde)之外,将形式和色彩运用到画布上的做法已经让位于新的和非传统的解决方案,那么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们见证了大多数艺术爱好者最喜爱的媒介的重新崛起。然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至少在最初阶段,绘画必须接受与几十年来使其边缘化的实验的妥协。从本质上讲,为了重返当代舞台,绘画必须接受不在画布上作画的外在形式,至少在最初阶段要超越二维的概念,颠覆与观众之间通常的空间关系。
在意大利,这一混合潮流的主要诠释者无疑是鲁道夫-斯汀格尔(Rudolf Stingel,1956 年生于梅拉诺)。这位出生于南蒂罗尔的画家于 1989 年开始崭露头角,当时他制作了一本指导手册,说明如何创作他的抽象画。1991 年,他开始使用地毯,在纽约的丹尼尔-纽伯格画廊(Daniel Newberg Gallery),地毯在白色的画廊中以鲜艳的橙色显得格外醒目。两年后,他在威尼斯双年展上以类似的方式重复了这一实验。2000 年代,他继续进行实验,使用泡沫塑料和赛璐珞等不同寻常的媒介制作绘画装置,并寻求公众的参与(见关系艺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位画家越来越多地 “清理 ”他的绘画作品,更频繁地将其带入画布和具象主义(《无题(山姆之后)》)的常规轨道,但并没有放弃抽象主义或使他成名的各种实验。例如,2013 年,他用东方图案的地毯铺满了整个威尼斯格拉西宫。
罗伯托-库奥吉(Roberto Cuoghi,1973 年出生于摩德纳)的创作间隙也许更为宽广。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从雕塑到表演,从摄影到音乐,他至少尝试过 19 种不同的媒介。其中包括绘画,他以不同的方式诠释绘画:表现主义、流行、抽象、超现实主义。他的作品总是技术精湛,审美大胆。例如 2003 年的《无题》(带邮票的黑色地球仪) ,他使用从石墨到缎面有机玻璃等各种材料描绘了一幅抽象的风景画。还有《D+P(XIXA)mm》(2010 年),这是一幅用粉笔、粉笔和压缩空气在纸上和聚丙烯酸树脂上绘制的双联画,描绘的是一个人在看似两个盘子上的形象。尤其是近年来,他的绘画越来越多地关注肖像画,如 2020 年的《P(XVPs)po》,往往是一种幻觉和麦角症式的诠释,或者是现实生活中的抽象主义,如 2022 年的《P(XLVIIIPs)po》,或者是固有的纹理。
Pietro Roccasalva(莫迪卡,1970 年)也走过类似的道路,尽管他的作品没有那么夸张,在概念上也更接近绘画。与上述同行一样,洛卡萨尔瓦也喜欢兼收并蓄的风格和技巧,他能够在各种风格和诗学之间游刃有余,糅合了众多建议,最终找到了自己独特的声音。对他来说,引文主义不是修辞学,而是在非常遥远的风格形式(亚述、立体主义、新古典主义、文艺复兴)之间产生交集的机会,以产生瞬间或持久的接触点,产生带有神秘火花的美学短路。为什么一只公鸡穿着瑞士卫兵的衣服(《无题》,2010 年)?为什么《西方新娘》(2021 年)似乎是网球拍的镜像,而网球拍的弦交织成一种曼陀罗?为什么在形而上学的《无题(嬉戏七)》(2020 年)中,奇异建筑的穹顶让人联想到榨汁机?在这幅如迷宫般流动的画作中,答案寥寥无几,却蕴含着无数诗意的暗示。
乔瓦尼-弗兰吉(Giovanni Frangi,1959 年出生于米兰)的绘画原教旨主义更为明显,他也曾多次尝试雕塑创作。2001 年,维罗纳美术馆(Galleria dello Scudo di Verona)在米兰当代艺术博览会(Miart)上的展台是两者对话的象征。然而,弗兰吉在以自然主义为主题的画作中找到了自己完整的风格印记,在这些画作中,自然在色彩和形式上表现出了自己的变化,在一个模棱两可的山脊上移动,这可能会让人想起高更的色彩主义诠释(《达恩赛公园》)和美国的色域(《Usodimare》,2016 年)。为了进一步缩小领域,使我们更接近当代,更具代表性的作品是自然元素似乎悬浮在抽象主义的深渊之上(《La legge della giungla》,2015 年)或完全被其抛弃(《Settembre》,2016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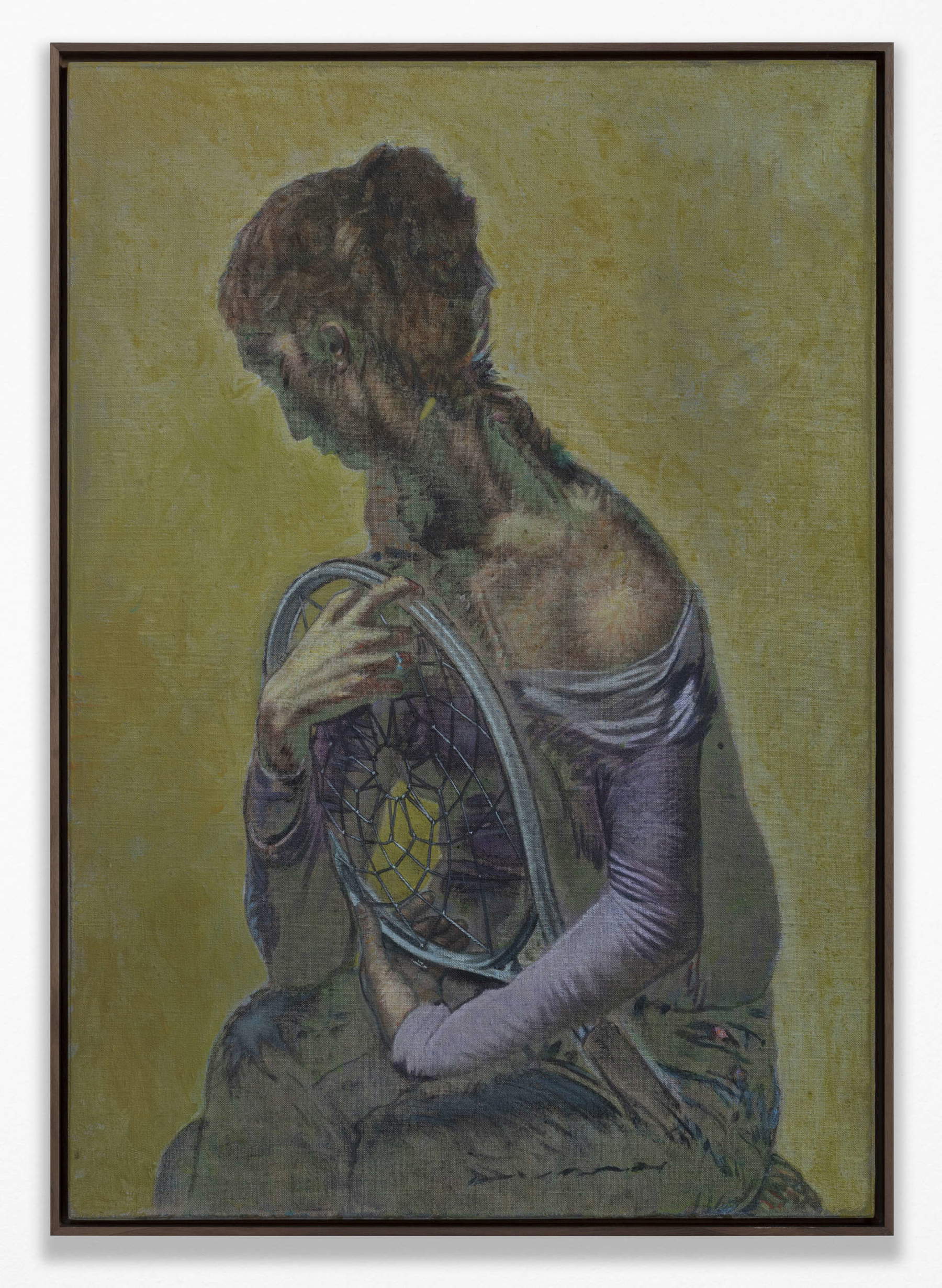



尼古拉-萨莫里(Nicola Samorì,1977 年出生于弗尔里)与弗朗吉一样擅长使用画笔,也是从绘画与雕塑之间的平衡入手。艺术家从临摹作品,尤其是 16 和 17 世纪的作品入手,对其进行改造和重新诠释,甚至扭曲其本质。肖像画尤其受到影响,脸部经常被遮住(《关于非洲人》,2013 年;《JV》,2009 年)或留下伤疤(《Penthesilea》,2018 年)。他直接阐述了自己的意图:“我鞭打绘画是为了让它流血,因为我认为它就像一具身体,被当作贫血的有机体,而实际上它根本不是。图像及其叙述对于这个需要肉体隐喻来明确自身的场景具有功能性”。
帕特里齐奥-迪-马西莫(Patrizio Di Massimo,杰西,1983 年)的作品也唤起了人们对历史的回忆,在戏剧基调上与巴洛克风格相近。然而,就内容而言,这些作品显然坚持了当代性,展现了日常生活的瞬间,画家以饱和的超写实主义风格将这些瞬间升华为诗意的瞬间。此外,他还经常将自己作为家庭和普通场景的主角,时不时地将自己置身于截然不同的环境中,在艺术参照(《与菲利普-古斯顿的自画像》,2022 年;《包豪斯》,2019 年)和一种不安的维度之间摇摆不定,既立足于现实主义,又对清醒的超现实主义潮流眨了眨眼睛(《蓝色房间》,2021 年)。
与迪-马西莫一样,近年来还有其他一些画家成功地在新绘画语言的作者群中脱颖而出,他们的作品大多有效地融合了当代内容和形式主义,并与 20 世纪的作品相呼应。其中,鲁迪-克雷莫尼尼(Rudy Cremonini,1981 年出生于博洛尼亚)擅长使用油画颜料。因此,画作是自由的、流动的,沉浸在梦幻般的氛围中,让人联想到我们在睡眠中经历的事件,没有确切的存在界限。它唤起了我们的想象、记忆、恐惧和不安全感所产生的共鸣。克雷莫尼尼通常对被限定或封闭的生活空间感兴趣,他描绘了家庭环境中的人类主体(The lord of the archive,2019 年)、动物园中的动物(I am a flamingo in your eyes,2015 年)、温室中的奇异植物(Pinkcactus,2018 年)或狭小到被限制的景观特写(Intricate,2021 年)。植物和梦境也是托马斯-贝拉(Thomas Berra,Desio,1986 年)的主题,这位艺术家触及了当代绘画的另一个基本点,不仅是意大利绘画:取消具象和抽象之间的区别。在这第三个维度中,贝拉的作品诞生于前两个维度的辩证冲突之中,他既选择了人类为主题(通常以二维、本质和最小化的方式呈现,如《Non c’è niente che sia per sempre》(2021 年)),也转向了植物世界。特别是,后者是他自 2015 年以来一直关注的研究课题。另一方面,这也是他风格的完美研究空间,让他有机会与现实联系,以及确定抽象的模式或沉醉于涣散的符号和旋转的色彩的流动(《赞美流浪者》)。
在Guglielmo Castelli的画作(都灵,1987 年)中,身体、空间和物体也相互渗透。作者以私密和个人化的手法,营造出极具戏剧深度的情境,将明快的美式色彩与欧式象征主义暗示相结合。他的画总是披着一层忧郁的面纱,尽管从抽象画固有的概念出发,如色彩层次的分布和平衡、物质、物质的过度和去除,但他的画却是具象的。为此,卡斯泰利的作品与画布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以表演的方式接近画布,从不同的角度与画布互动。因此,再一次显而易见的是,经过深入分析,每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无论是古老的还是当下的,都将被铭刻在一种流动之中,其中的奇异之处很难被分离出来。每一种经验都与一种语境相吻合,而这种语境可以无限扩展,可以无限建立联系,可以无限恢复参照。这使得历史学家和评论家的任务变得尤为艰巨--他们被要求从这种流动中选择画面,凝固元素并将其提升为象征更复杂的事件核心。我们已经尝试过了,但我们意识到,分析如此近距离的时代,也许近得无法聚焦,更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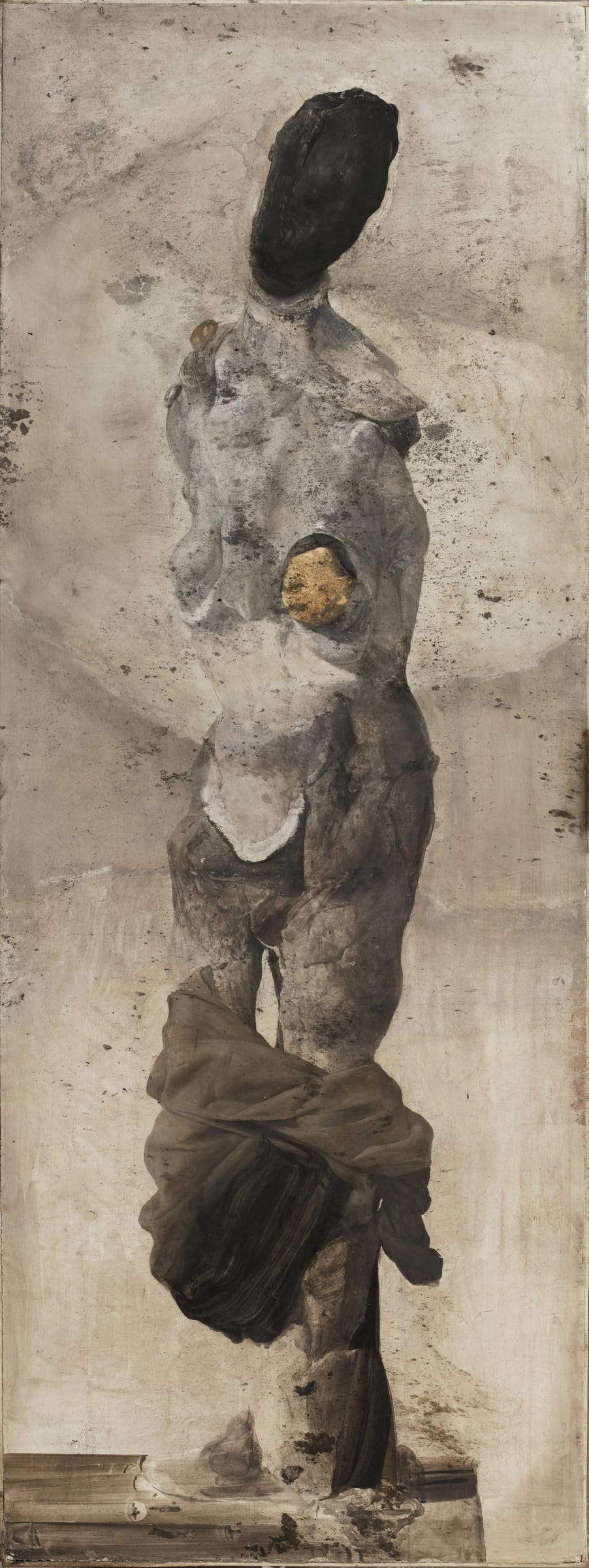






免责声明:本篇意大利语原文的中文翻译由自动工具生成。 我们承诺会对所有文章进行审核,但无法保证完全避免因软件造成的翻译误差。 您可以点击 ITA 按钮查看原文。如发现任何错误,请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