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佐-库奇(Enzo Cucchi)会说,我们已经进入了装点门面的时代。六十多年前,伊塔洛-克雷莫纳(Italo Cremona)就用过这个名词。那是 1958 年,克雷莫纳在《咖啡馆 》上撰文(阿尔巴西诺称其为 “嘲笑和揶揄的杂志”:他也在该杂志上撰文),并与莱昂内尔-文丘里展开论战,文丘里认为克雷莫纳是在为 “古典和人文时代与自然的对话 ”吟诵葬礼赞美诗,这在复活节周一的郊游活动中是最合适的。文丘里说:“今天的人类自言自语,并以此创造了自己的世界,足以让他生活、思考和飞翔。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想象力也更喜欢独白,也就是说,它不需要没有人相信的自然事物来表达自己,这难道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对文图里来说,这就是抽象艺术的原因,也是适合现代文明需求的艺术的原因。克雷莫纳的观点与文丘里完全相反,他甚至对文丘里模糊 ”自然 “的含义提出了质疑。克雷莫纳认为,无视视觉和触觉的绘画就是抽象画的观点是鲁莽的,因为我们也知道有一些二维作品包含了相同的物体:克雷莫纳指责这种抽象艺术观念是 ”橱窗装饰",因为他认为作品的手段就是橱窗和装饰的元素。如果我们谈论装饰,那也无可厚非。当我向库奇询问他在纽约维托-施纳贝尔(Vito Schnabel)画廊举办的新展览时,他告诉我,装饰也有自己的尊严。我是在他罗马的家中见到他的,他刚从美国回来。采访他的意图也很明确。
在我开始问他一些问题之前,他就开始和我谈论商店的橱窗和橱窗设计师。我只是告诉他,我读过他的展览介绍,或者类似的内容。甚至谈论装饰也会很有趣。问题是,在他看来,如今缺乏思考。“如今有一种所谓的当代艺术,它是巨大的,比拼的是谁能拍得最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它背后的东西并不重要。即使是主题,也没有人关心。重要的是它有一定的质量。是装饰吗?甚至不是:如果能对装饰进行伟大的反思,那将会非常有趣。都一样:疯狂。对 Cucchi 而言,”橱窗装饰 "是同质化,是缺乏意识。艺术变成了消费的对象,艺术是为了展览而不是为了被理解,这是艺术家的命运,他甚至不再是创作过程的中心,往往被委托给他人。这是一种不靠思想维系的艺术,这是一种不靠惊奇维系的艺术,这是一种惰性艺术,它无法让任何人说话,无法让公众说话,更无法让评论家说话。它不再行使自己的职能,放弃了自己的特权,甚至可能不再关心,因为它已经改变了自己,躲到了所谓的策展人这个更舒适的地方。
库奇认为,“装点门面 ”是不一致和肤浅的表现。他会说是 “粗心大意”,而且他热衷于告诉我,粗心大意是他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事情,甚至在他去买报纸的时候也是如此(旁白:“报社告诉我,我们两个人买报纸:她每天早上都用自己仅有的一点钱去买《晚邮报》,我想知道这怎么可能”)。现在,从未有幸拜访过恩佐-库奇(Enzo Cucchi)的人一定知道,要去拜访他,你必须经过一些纪念碑前,而当你在寻找前往他家的捷径时,必然会绊倒这些纪念碑。万神殿、纳沃纳广场、圣天使堡、Ara Pacis、San Luigi dei Francesi、Sant’Agostino、San Salvatore in Lauro:要去恩佐-库奇的家,就必须经过这些地方。“他说:”这座城市吞噬了一切。它吞下了所有能吞下的东西。它是一个伟大的娼妓,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能像罗马这样吞下如此多的东西,它是一个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城市。在罗马什么都不会发生,但什么都会发生。它是一个巨大的垃圾箱。但它也是一个美妙的垃圾箱“。正是在这污秽之中,才潜藏着非凡。圭多-皮奥维内(Guido Piovene)曾经说过,罗马是一座充满反义词的城市,这座城市就像’一座森林,人类的欲望在森林中徘徊、争斗’,在森林中,人们自然希望找到一切,包括奇妙的事物。库奇认为,问题在于奇妙不再是奇妙。”每天,我都会穿过我的街区,路过纳沃纳广场。你不知道我看到了多少人。罗马是一个大省,因为每个人都从意大利和世界各地来到这里,不知道要做什么。但似乎没有人注意到周围的一切。相反,他们根本不在乎。我宁愿关注这些"。言下之意是:不管是谁写东西,最好都是在处理来自惊奇的荒废,而不是我们这个渺小、愚钝、胆怯的艺术世界的大使们。

让我们达成共识:恩佐- 库奇关于当今艺术的思想早已被记录在案,也许根本没有必要进一步阐述。然而,库奇仍有办法触及新的高潮。“你看,”谈了大约二十分钟后,他告诉我(我心目中的采访还没有开始),"这个问题与每个人都有关。即使是你。你经营着一本美术杂志,你当然会给我一个好的采访。但更重要的难道不是毒害所有的艺术杂志吗?你可以开始,真正地毒害它们:比如,与其对我进行采访,我希望采访消失,没有采访。没必要这样。否则每次都是一样的,我说,我说......但我是谁?这有什么关系?所有的艺术杂志都会给我专访,让我说话,让我谈这个谈那个,谈我在纽约的展览......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就一个话题进行互动,并发展出其他的东西。
于是采访开始了。我都不记得自己准备了多久,但不管怎样,也许库奇是对的:对我来说,尝试接受邀请似乎更有吸引力。我可能不会成功,但我会试一试,然后我会试着勾画一下 "构思"(pars construens),或多或少笨拙地试图就 “惊奇 ”是什么展开讨论,我确信,通过与一个一生都在实践 “惊奇 ”的人聊天,那些读我们书的人可能会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博尼托-奥利瓦(Bonito Oliva)在跨文艺复兴时期的宣言中写道,他的新艺术的基础之一是 “艺术家对作品的惊奇,而这种惊奇不再是根据预期的确定性计划来构建的”。而是在他的眼前,在一只沉入艺术材料的手的推动下,在一种由理念和感性之间的体现所构成的想象中形成的"。
我想说的是,也许有点含蓄,对我(我想对每个人)来说,惊奇有多种形式。其中之一就是出乎意料的惊奇。当你去到一个你不了解的地方,一个你可能低估了的地方,然后在那里你发现了一些令人惊讶的东西,一些强大的东西,你就会惊叹不已。在我可以给他举出的成千上万个例子中,我带点恶意地举出乌尔巴尼亚的云彩圣母 像,部分原因是它是我最后写的一篇文章的主题之一,部分原因(或者说:最重要的原因)是恩佐-库奇来自马尔凯。乌尔巴尼亚的公爵宫与乌尔比诺更著名的公爵宫毫无关系。尽管乌尔比诺的最后一位公爵更喜欢乌尔巴尼亚(当时公爵们仍称其为卡斯特杜兰特),并死在了乌尔巴尼亚公爵府。后来,乌尔比诺被移交给了教皇国,这座吞噬一切的城市也吞噬了乌尔比诺公爵宫中的一切,首先是公爵的图书馆,这是当时欧洲最大的图书馆之一,藏书 15000 卷,几乎全部都在罗马,为乌尔比诺大学(Studium Urbis)提供了一个图书馆。教皇无限仁慈,允许乌尔巴尼亚保存其中的五百卷(不得不说,这些书至今仍在那里)。宫殿内所剩无几。因此,发现费德里科-巴罗奇(Federico Barocci)和工作室创作的《云中圣母》这样一幅画(而且,这幅画几乎是偶然出现在宫殿里的,因为在十七世纪,它还在其他地方)是令人惊讶的,尤其是当你在展览行程的最后,在最后一个房间里发现它时。它让你感到惊讶,因为这幅如此轻盈、如此精致、如此动人的画作,竟然留在了这座如此渺小、如此边缘化、在其历史上遭受过所有可能的创伤的城市里。而它却毫发无损。
为了留在马尔凯地区,留在一个只有几千居民的小镇,库奇向我讲述了洛伦佐-洛托(Lorenzo Lotto)在辛戈利(Cingoli)创作的《玫瑰圣母》(Madonna del Rosario )。他让我明白,对他来说,一种奇妙就隐藏在细节之中,这些细节让一个故事、一个建筑群变得连贯,也许是因为它们稀释了注意力,分散了对特定条件的关注,允许意义的转换,允许前所未有的开放。毕竟,奇妙也是一种争论的形式。库奇回忆起我记忆中的小天使,他们站在圣母脚下,从一个巨大的柳条筐中取出玫瑰花瓣,随处撒落。“他说:”这些花朵完全改变了神圣的场景,让上面的舷窗都看不清了。他用念珠的奥秘暗指这些场景。“这难道不是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吗?这不是一件非常现代的作品吗?我说的是花瓣。那些花瓣抹去了一切。你只看到花瓣,看不到后面的东西。或者说,你看到了它,但它被这种姿态完全改变了。我觉得这种姿态非常现代”。他想知道有多少人能理解这种姿态。他的理由是,也许他们很少注意到这一点。“我们的艺术朋友”,Cucchi 用这个词指的是以各种方式在我们的世界中出现的所有人,他称之为 “Circo Togni ”的内部人士和常客。或许所有在看台上观看马戏的人都会更加关注。或许他们根本就不在乎马戏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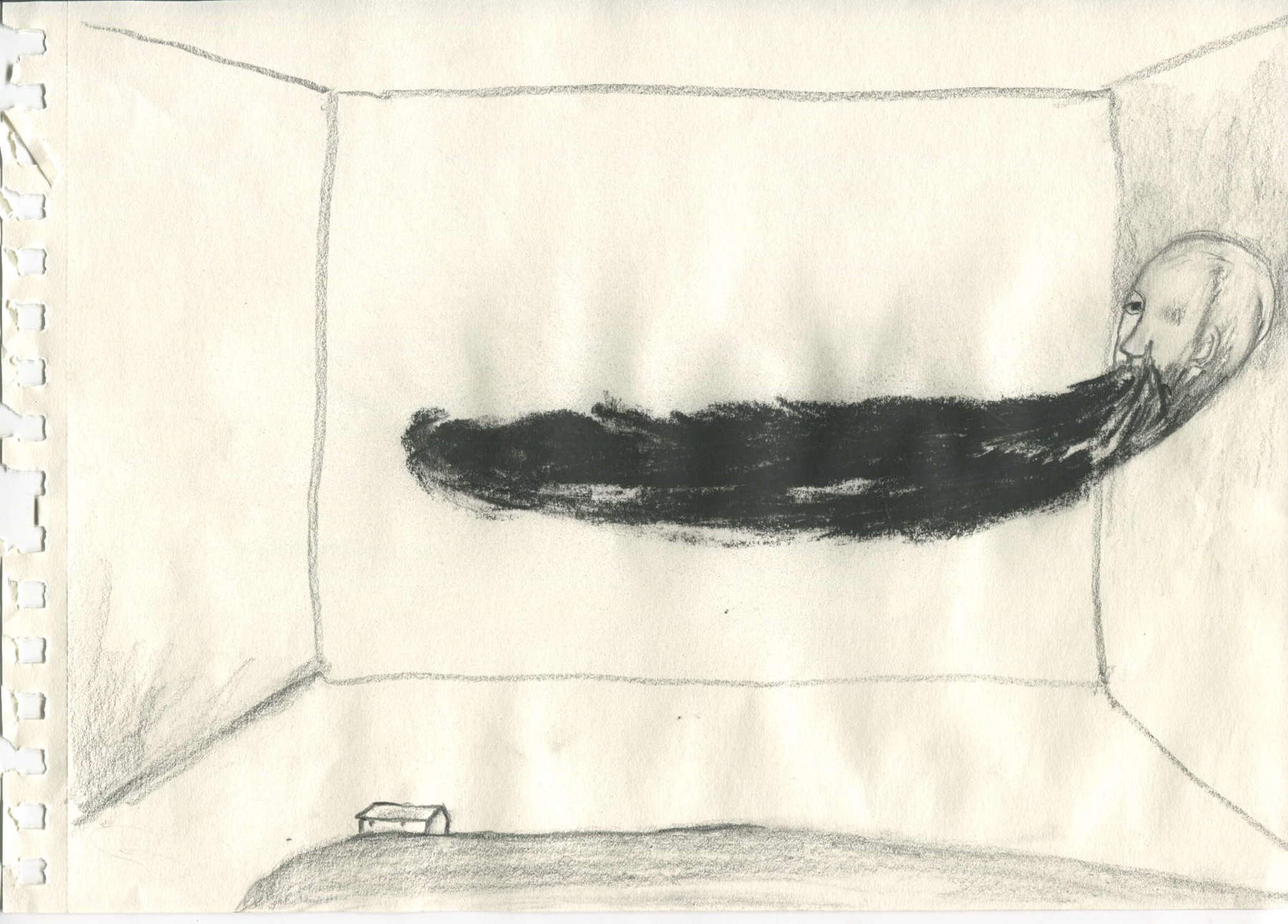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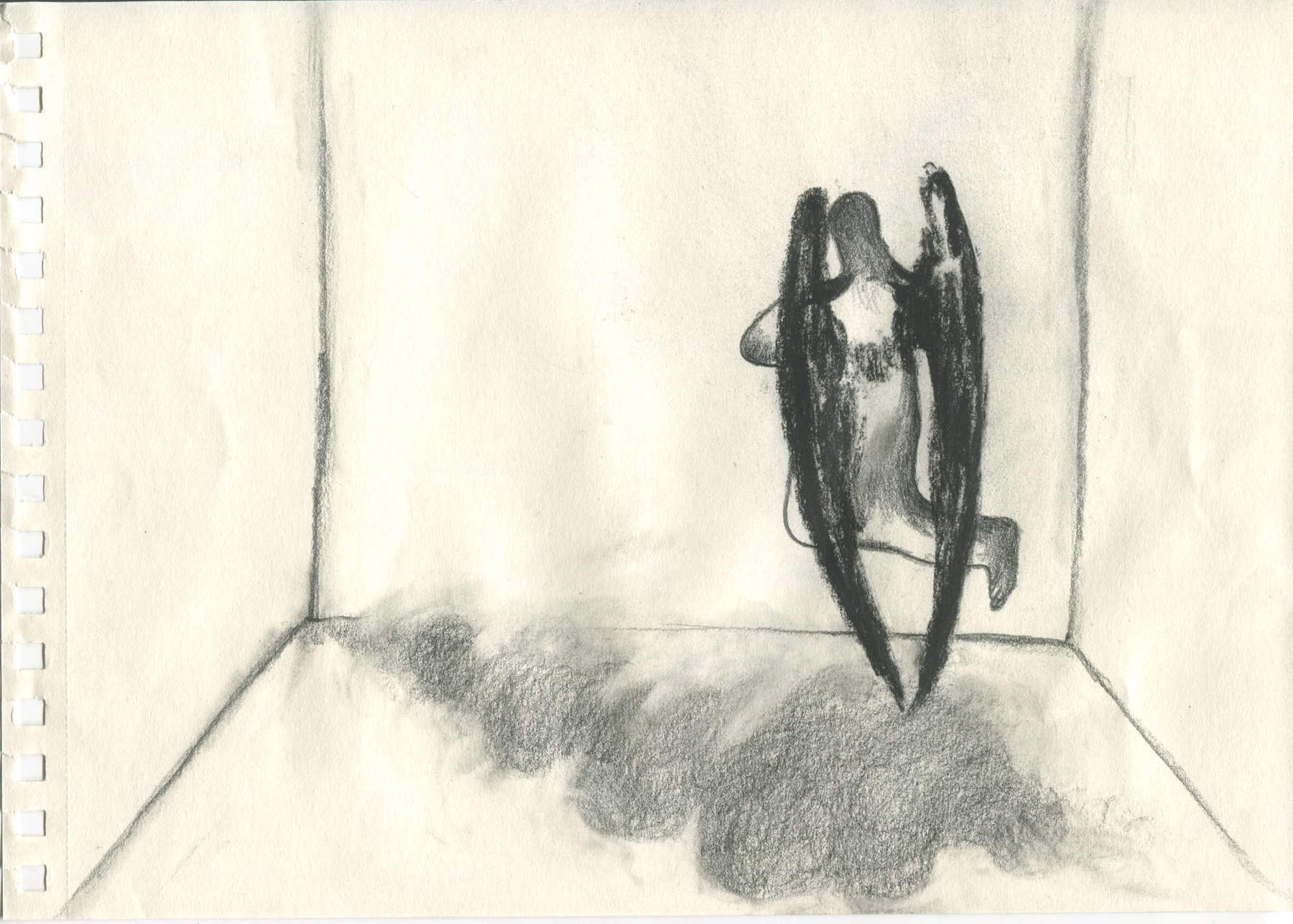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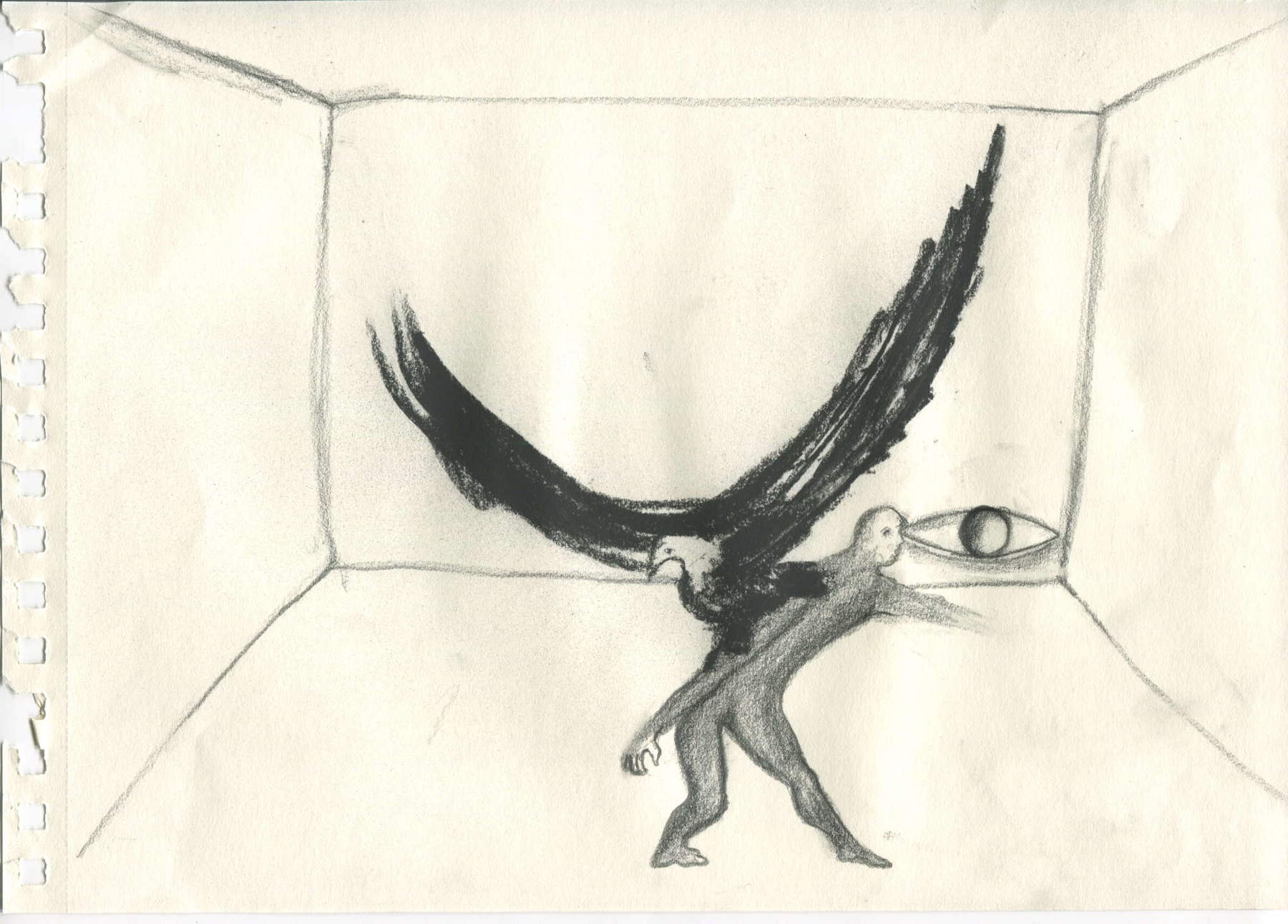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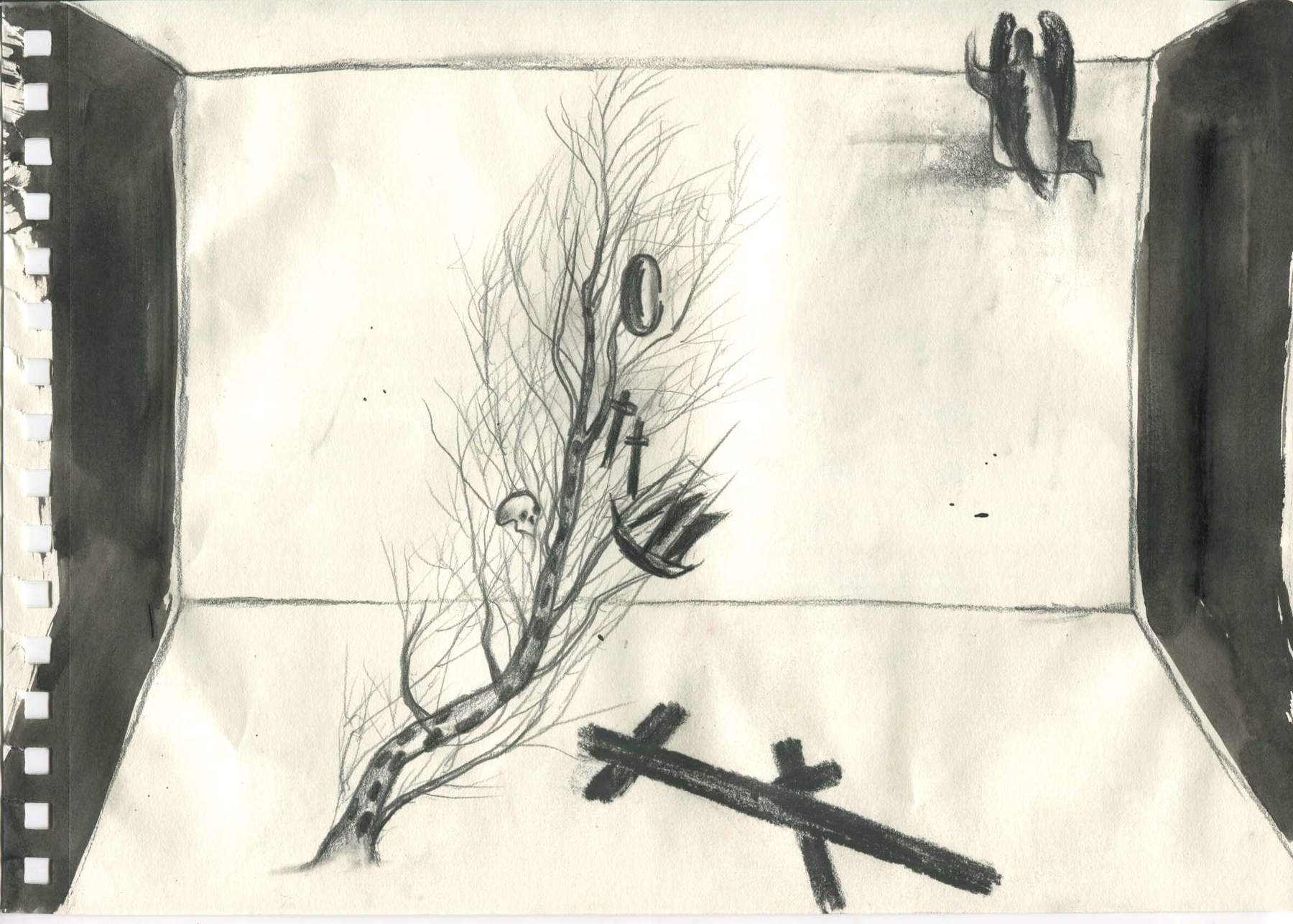

说到这里,库奇不能不提到皮耶罗-德拉-弗朗西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他非常珍视这位艺术家。"是谁拯救了帕尔多圣母院?农妇!那些小人物!我非常信任她们。因为我来自那里,来自一个农民家庭。通常,人们会有一种错觉,以为人们什么都不懂,但事实并非如此,我请你们把这一点写下来。有一件事一直让我感到惊奇,也从未让我感到无聊(通常让我感到无聊的是成人的事情),那就是当也许更简单的人类生物谈论某些事情时,比如我上小学三年级的父亲,或者我的母亲,她经常把东西从嘴里拿出来让我吃(我认为自己是个超常发挥的人,这也是为什么我对任何事情都不屑一顾的原因:这也是我对任何事情都不在乎的原因:因为从任何意义上讲,我拥有的都是最多的)。在这里:正是这些人,这些非常淳朴的人,一提到什么,他们就像孩子一样欢迎,因为他们的心是火热的"。据文献记载,18 世纪时,蒙特基市政府决定拆除帕托圣母所在的教堂,皮耶罗-德拉-弗朗西斯卡的壁画幸免于难:教堂的一部分保留了下来,改建成了一个小礼拜堂,皮耶罗的圣母被移到了高祭坛上方的壁龛里。自古以来,瓦尔蒂贝里纳的居民就赋予帕尔多圣母 以护身符的价值。托斯卡纳这片土地上所有信教的母亲都曾在帕尔多圣母像前祈祷,这幅壁画之所以能保存下来,也是她们的功劳。时至今日,仍有许多妇女前往蒙特尔奇的小博物馆,祈求这幅画像的保护、平安分娩,甚至仅仅是感到有人陪伴。我向库奇提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的一个小插曲,当时他们请求佛罗伦萨借出帕托圣母 像举办展览,但遭到了蒙特基市长的拒绝,因为居民们坚决反对:如果在没有壁画的日子里村里的孕妇遭遇不测,市长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我认为,还有另一种形式的惊奇,它不是意料之外的惊奇,也不是滑稽可笑的惊奇,更不是突如其来的惊奇,也不是宏大场面的惊奇。它是一种更谦逊、但更顽强的惊奇。这种奇迹潜藏在日常的褶皱之中,由微小的动作、共同的感官和忍耐力构成。这种奇迹不需要新奇。奇迹既是发现,也是认识。博尔赫斯在他的一篇《美国谈话录》中说,“对生活的惊叹可能是诗歌的本质”。我想到了这种惊叹。
恩佐-库奇(Enzo Cucchi)的许多画作都是在这片被日常奇迹灌溉的土壤上萌芽的。在纽约展出的最大画作是一幅两米多长的画布,朱红色的背景上有三个骷髅头,骷髅头 上交叉着一条橙色的带子。有些人可能会惊讶地发现,他的这些图像竟然来自于他认为非常普通的场景。“这是人人皆知的少数事情之一。这是世界上最平常的事情,”他说。“那不勒斯妇女在家里放一个头骨,她们在上面撒灰尘,然后在上面写下她们去玩乐透的号码。这是我们最熟悉的东西。就像问塞尚为什么画苹果一样:我也用我知道的东西。我尽量缩写,不去寻找奇怪的东西。我已经对我所知道的少数事情感到惊讶了。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哪些东西?我突然问库奇,他是否是信徒?他与神圣有什么关系?”我希望我知道,如果能知道所有这些事情,那将是一件美妙的事情。这些东西是如此特别。我觉得神圣的规则很奇妙,但我依赖那些比我更了解这个主题的人。例如,我曾与罗伯托-塔利亚费里(Roberto Tagliaferri)[神学家,编者注]合作过,我们不仅是朋友,还成为了好朋友,但这仅仅是因为我告诉他:’听着,你很擅长解释神圣的规则,擅长描述等等,但我不想与你有任何瓜葛’。’而他则更加友善,因为他告诉我:’我也不想和你有任何瓜葛’。但实际上,我们一直在聊天。当他写作时,他提出的论点是如此特别,如此精确,如此睿智,如此具体。但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他对神圣的事物非常了解,而且善于表达。我惊叹不已。对我来说,这就是神圣。



我们一致认为,奇迹不是教育的问题。Cucchi 补充说,艺术就更不是问题了(他告诉我,“对于艺术,要么你会眼前一亮,要么你不会”)。他认为,很多人 “深入浅出,游刃有余,甚至有很强的能力,但仍然干巴巴、平平淡淡,这让人印象深刻,从人性的角度来说,我也很遗憾,但我们必须告诉他们,因为如果我们不告诉他们,就会弄得一团糟”。不过,在我看来,对他来说,缺乏好奇心是缺乏习惯的问题,而不是缺乏敏感性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他喜欢回顾曼加内利在他的一篇题为 "疯狂的机器"(La macchina maniacale)的文章中所写的东西。曼加内利说,他既不是建筑师,也不是建筑历史学家,他只是一个热爱建筑的人,即使建筑并不热爱他。“他在文章中写道:”房子不是用来做梦的。人的梦想是糟糕的、艰难的,就像穿着紧鞋走路一样。所有的房子都是这样吗?我敢说在所有的房子里。但究竟是什么让这些房子变得情感贫乏、幻想空洞、对梦想有害呢?在我看来,是角落的发现。如果我回想一下我生命中的所有房子,我首先看到的是数不胜数、令人难以置信的角落。所有的房间都是正方形或平淡无奇的长方形。我不记得有任何例外:即使有,也顶多是精确到毫米的曲线,即柏拉图的曲线概念。总之,我不记得有任何曲线。[......]一个正方形的房间,一个长方形的平面,会给人一种可知、可解释的错觉:在这类房间里没有藏身之处。为了梦想,曼加内利需要暧昧、变形、迷宫般的地方,让人迷失,让人滑倒,让人发现。从本质上说,在那里人们会感到惊奇。几年前,有人做过一项调查(YouGov 为威卢克斯做的调查,想了解的人可以谷歌一下),结果显示,如今人们平均有 90% 的时间是在室内度过的。可以说是在角落里。
事实上,库奇的房子比人们通常看到的要少一些角落,我不知道这是否只是巧合。但我并不想研究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不过,我有兴趣从他那里了解新奇是如何从惊奇中产生的。或者说:我有兴趣了解他的经验、他的立场。我知道我已经脱离了避免访谈的目的,脱离了就某个话题进行互动的目的,因为这是一个典型的访谈问题。但我认为,这个问题还是与我们互动的话题有关,而且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可以为我们的谈话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他的回答在我看来是一种行动的号召。“我不认为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他对我说,暗指那些与他共同经历历史时刻的其他艺术家,“认为或想象我们在做一些新的事情,那完全是天真。我们会接手一些缺失的东西,出于好奇去做。当空气中弥漫着某种东西时,这种东西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存在的,有些人出于需要,会在不经意间捕捉到这种东西。但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什么。当你捡到东西时,你是出于无奈,因为你想做那件事,因为你想看那件事。所以你就做了”。
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我们的纸质印刷杂志 Finestre sull’Arte第 26 期上 ,错误地以简写形式发表 。点击此处订阅。

本文作者 : Federico Giannini
Nato a Massa nel 1986, si è laureato nel 2010 in Informatica Umanistica all’Università di Pisa. Nel 2009 ha iniziato a lavorare nel settore della comunicazione su web, con particolare riferimento alla comunicazione per i beni culturali. Nel 2017 ha fondato con Ilaria Baratta la rivista Finestre sull’Arte. Dalla fondazione è direttore responsabile della rivista. Nel 2025 ha scritto il libro Vero, Falso, Fake. Credenze, errori e falsità nel mondo dell'arte (Giunti editore). Collabora e ha collaborato con diverse riviste, tra cui Art e Dossier e Left, e per la televisione è stato autore del documentario Le mani dell’arte (Rai 5) ed è stato tra i presentatori del programma Dorian – L’arte non invecchia (Rai 5). Al suo attivo anche docenze in materia di giornalismo culturale all'Università di Genova e all'Ordine dei Giornalisti, inoltre partecipa regolarmente come relatore e moderatore su temi di arte e cultura a numerosi convegni (tra gli altri: Lu.Bec. Lucca Beni Culturali, Ro.Me Exhibition, Con-Vivere Festival, TTG Travel Experience).
免责声明:本篇意大利语原文的中文翻译由自动工具生成。 我们承诺会对所有文章进行审核,但无法保证完全避免因软件造成的翻译误差。 您可以点击 ITA 按钮查看原文。如发现任何错误,请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