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节选自普拉菲尔派展览目录中的评论文章。现代文艺复兴》由詹弗兰科-布鲁内利(Gianfranco Brunelli)指导,伊丽莎白-普雷特约翰(Elizabeth Prettejohn)、彼得-特里皮(Peter Trippi)、克里斯蒂娜-阿西迪尼(Cristina Acidini)和弗朗切斯科-帕里西(Francesco Parisi)策展,蒂姆-巴林杰(Tim Barringer)、斯蒂芬-卡洛威(Stephen Calloway)、夏洛特-盖尔(Charlotte Gere)、维罗妮克-杰拉德-鲍威尔(Véronique Gerard Powell)和宝拉-雷菲斯(Paola Refice)担任顾问,在福尔利的圣多梅尼科市政博物馆展出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
1899 年,威廉-迈克尔-罗塞蒂(William Michael Rossetti)在与其他六位年轻人共同创建拉斐尔前派兄弟会51 年后回忆道:“经过几年的学术训练后,这些年轻人的脾气就是叛逆者的脾气:回想 1849 年春,兄弟会的画作首次公开展出,他描述道:”一群不安分、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决心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扫除某些低迷的体面"。每一代人都会产生不满的年轻人,西方艺术史上也有一系列的叛乱,有些叛乱的影响更为持久。然而,兄弟会的反叛并不仅仅关乎美学。他们推崇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后者在其影响深远的著作《过去与现在》(1843 年)中指出,英国民族必须 “学会理解其陌生而崭新的今天的意义”。英国,尤其是前拉斐尔派所居住的伦敦,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全球帝国的中心,与世界紧密相连,但却面临着深刻的内部变化:崛起的中产阶级繁荣昌盛,而工人却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他们往往生活在拥挤的城市和以牺牲自然为代价扩张的工业中心。鉴于这种不稳定的背景,蒂姆-巴林杰和杰森-罗森菲尔德将拉斐尔前派兄弟会认定为一场前卫运动,“推翻当前的艺术正统,代之以新的批判性实践,往往直接面对当代世界”。1848 年,欧洲大陆爆发了革命,而在英国,革命的变种 “宪章派 ”运动(Chartist movement)的暴力程度较低,它呼吁制定 “人民宪章”,保证所有 21 岁及以上的男性都有选举权和无记名投票权。1848 年 4 月 10 日,皇家学院的两名学生威廉-霍尔曼-亨特和 约翰-埃弗里特-米莱斯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大规模宪章派示威游行 。
正如伊丽莎白-普雷特约翰(Elizabeth Prettejohn)所写的那样 ,"年轻的拉斐尔前派对维多利亚时期艺术体制的反抗在现代艺术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是自上而下的攻击“。对他们来说,’以[埃德温]-兰德塞和[查尔斯-罗伯特]-莱斯利等皇家学院的知名人士为代表的体制,意味着通过描绘适合富裕资产阶级家庭环境的愉悦和轶事题材而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前拉斐尔派采用比兰德塞尔的狗和莱斯利文学作品中有趣的场景更严肃、更高雅的题材,表达了对老一辈艺术家的含蓄批评”。因此,拉斐尔前派从一开始就选择了与道德、宗教、社会和政治主题直接相关的题材,这些题材对他们来说具有迫切的意义,但对大多数公众来说却是陌生或令人不安的,他们采用的构图和技法既有历史依据,又具有实验性。与莱斯利-奎恩精心创作的油画《凯瑟琳与耐心》(Katherine and Patience)相比,他们的创新更加明显,这幅画描绘的是莎士比亚戏剧《亨利八世》中的一个场景。这幅作品以其内敛的色调和令人印象深刻的明暗对比,体现了传统叙事艺术的特点,在英国皇家学院夏季画展上受到了中产阶级买家的青睐;事实上,这幅画被利兹市的实业家约翰-谢普申克斯(John Sheepshanks)买下,十五年后,他将自己收藏的此类画作捐献给了国家。莎士比亚是拉斐尔前派的偶像之一,我们稍后会看到他们对莎士比亚情节的诠释有多么大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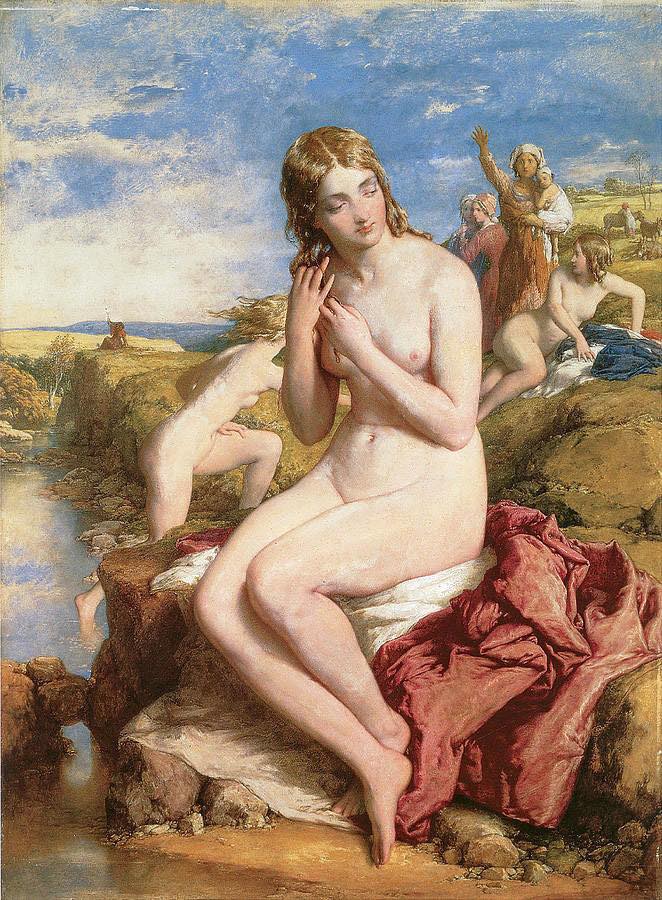

威廉-迈克尔-罗塞蒂(William Michael Rossetti)的上述 1899 年回忆录是在事件发生数十年后撰写的,因此在阅读时应考虑到这一点。霍尔曼-亨特的回忆录也是如此,他在 19 世纪 80 年代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并于 1905 年出版了一卷回忆录;然而,当他写到在 20 世纪 40 年代他钦佩莱斯利以及威廉-埃蒂、威廉-穆尔里迪和奥古斯都-利奥波德-埃格等其他成功学者的技术水平时,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的说法。无论如何,在亨特看来,几乎所有在皇家学院参展的艺术家都是’陈腐而做作的;在我眼里,他们最常见的缺点就是用空洞的漂亮取代了美[......]。那些扮演人类角色的彩绘蜡像让我恼火,平庸的传统常常让我远离那些我原本欣赏其优点的大师“。关于学术技巧,威廉-迈克尔-罗塞蒂(William Michael Rossetti)写道,兄弟俩 ”憎恶那些仅仅是光鲜亮丽和优美的表现形式,以及那些渴望精湛却草率和近似的表现形式,或者正如他们所说的’邋遢’"。
参加 1848 年秋天第一次会议的七位年轻人来自不同的中产阶级背景,艺术能力也大相径庭。米莱斯、亨特和但丁-加布里埃尔-罗塞蒂都在皇家学院学习;罗塞蒂只是偶尔参加,而且在执行方面很吃力,而米莱斯是个早熟的天才,11 岁就被破格录取,因此领先于他的朋友们。与这三位领军人物齐名的还有雕塑家托马斯-伍尔纳(Thomas Woolner)、两位天赋较差的画家 詹姆斯-科林森(James Collinson)和弗雷德里克-乔治-斯蒂芬斯(Frederic George Stephens),以及加布里埃尔的弟弟威廉-迈克尔(William Michael);后两人后来转向艺术评论,并成为兄弟会的主要记录者。兄弟会的成员都很年轻,因此他们的聚会非常热闹,甚至可以说是歌舞升平。亨特回忆说,是加布里埃尔提议成立 “联谊会 ”的,因为他从意大利革命家父亲那里继承了对阴谋诡计的喜好;这就更加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既没有发表书面宣言,也没有创作集体肖像,只是在绘画中相互描绘,传达出他们年轻时的热情。[...]
正如亨特回忆的那样,兄弟俩欣赏的不是学院派课堂和画廊中追求的理想化和其他常规,而是十五世纪艺术 “如此充满活力和创新 ”所特有的 “坦率表达的天真特征和自发的优雅”,这种艺术在透视规则确立之前就已蓬勃发展。正如伊丽莎白-普雷特约翰(Elizabeth Prettejohn)所言,当时大多数英国艺术家都认为15 世纪早期的意大利(和弗拉明戈)绘画只是通往所谓的高级文艺复兴时期更复杂艺术道路上的一个探索阶段。当这七位朋友计划叛乱时,加布里埃尔提出了 “早期基督徒 ”这一术语,这是他从老师福特-马多克斯-布朗那里学来的,布朗与加布里埃尔志同道合,曾在意大利工作,但从未正式加入兄弟会。亨特建议用 “拉斐尔前派 ”来代替;他后来回忆说,他和米莱斯都非常欣赏拉斐尔为西斯廷教堂挂毯和亚历山大的圣凯瑟琳绘制的漫画,而他们认为《变容祭坛画》(由助手完成,两位年轻的英国人通过一幅版画了解到这幅画),“拉斐尔的漫画其宏大的漠视真理的朴素、使徒们华而不实的姿态和救世主毫无灵性的姿势”,标志着 “意大利艺术颓废的决定性阶段”。当两人向学院的一些同学表达这些想法时,他们回答说:“但你们是拉斐尔前派”。米莱斯和亨特’笑着同意必须接受这个名字’,于是这个名字最终与’Confraternity’合二为一。
亨特在他的回忆录中继续指出,“博洛尼亚学院流传至今的传统是后来所有流派的基础,并得到勒布伦、杜弗雷斯诺伊、拉斐尔-门格斯和约书亚-雷诺兹爵士的支持,这些传统产生了致命的影响,有扼杀绘画气息的趋势”。除了这个问题重重的血统之外,彼得-保罗-鲁本斯(Pieter Paul Rubens)还可以再加上一条:在他抄写的安娜-詹姆森(Anna Jameson)广为流传的《神圣与传奇艺术》(1848 年)一书中,加布里埃尔(Gabriel)每出现一个佛兰德斯大师的名字,都会在空白处注明 “吐在这里”。不可否认,鲁本斯的技艺精湛,但对他来说,鲁本斯代表了 学术体系中所有过分和庸俗的东西。因此,兄弟会拒绝了雷诺兹制定的教学大纲,包括需要临摹的石膏模型、裸体模特和 16 世纪后的色调。然而,威廉-迈克尔(William Michael)警告说:"如果认为他们自称为前拉斐尔派,就不认真欣赏拉斐尔的作品,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们决心通过个人学习和实践来发现自己的不同能力和潜能,而不受基于拉斐尔或其他任何人作品的规则和假山的束缚。除了自己的头脑和双手的能力以及对自然的直接研究之外,他们没有其他的主人[......]。这必须是深刻的,并具有最高程度的代表性(至少在自律和工作的初始阶段)。
在努力提高 “头脑和手的技能 ”的过程中,共同绘画--以及对画册进行评论--被证明对兄弟会的团队精神至关重要。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是Cyclographic Society 的成员,这是一个成立于 1848 年初的绘画团体。在第一次会议上,兄弟俩研究了卡洛-拉西尼奥(Carlo Lasinio)根据比萨坎波桑托壁画绘制的一卷版画,这些壁画出自贝诺佐-戈佐利(Benozzo Gozzoli)、奥卡尼亚(Orcagna)和乔托(Giotto)等艺术家之手。从这些作品的图形风格中可以发现拉西尼奥的痕迹,即强烈的线性、没有阴影和刻意的笨拙。他们采用这种方法,与其说是为了再现古代艺术,不如说是为了摆脱学术体系强加给他们的优雅和准确的造型习惯。亨特和加布里埃尔在 1848 年夏天编制的 “不朽者名单 ”中已经可以看出这种不一致性:这份由 50 多位 “英雄 ”组成、按五个等级排列的名单(其中只有耶稣基督被评为四星)虽然奢侈且自相矛盾,但却让我们了解到这些相当国际化的年轻人的品味。不仅有艺术家,还有诗人,包括但丁、薄伽丘、莎士比亚、济慈和丁尼生;15 世纪的有吉贝尔蒂、贝托-安杰利科和贝利尼,但也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如拉斐尔、莱昂纳多、“迈克尔-安杰洛”、“乔治亚尼”、提香和丁托列托。名单中还包括早期哥特式建筑师,但也可以提及其他明显的参考资料,如凡-艾克、丢勒以及绘制手稿、微型画和中世纪彩色玻璃的匿名作者,如果没有现代灵感来源,如摄影和仍活跃在罗马的拿撒勒画家的话。[...]







1849 年 5 月,亨特兄弟让英国艺术界第一次领略到了他们的创造力: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评委会将亨特的《里恩兹》和米莱斯的《伊莎贝拉》选入其著名的夏季展览。除了这两幅画之外,加布里埃尔的《圣母玛利亚的少女时代 》也参加了附近的自由画展(因为没有评审团而得名)。四位艺术家的作品首字母都是 PRB。(拉斐尔前派兄弟会),以模仿皇家院士的特权标记 RA.(皇家学院院士)和 A.R.A.(皇家学院副院士)。在 1849 年及其后的几年里,参观展览的人们无法忽视艺术史学家约翰-克里斯蒂安(John Christian)所说的拉斐尔前派绘画的 “春天般的清新”。即使在今天,这些画作的光辉和情感力量也会让人心跳加速,当年许多评论家都称赞艺术家们的雄心壮志和严肃态度。一些观察家对尖锐的线条、刻意的古风、令人不安的光线均匀度以及整个绘画表面的细节(后者更多来自佛兰德斯而非意大利)持保留意见,但他们并不了解该团体缩写的无礼之处,因此并未引起轩然大波。[...]
多年来,兄弟俩撰写了诗歌、散文、评论、目录条目和自己的小册子,并为自己的画作和画框题词。1849 年 5 月 15 日,在兄弟会的首批作品向公众展示后不久,威廉-迈克尔开始为该团体写日记,直到 1850 年 4 月 8 日,每天都有日记记录,此后日记的记录越来越少,直到 1853 年 1 月 29 日才完全停止。威廉-迈克尔还担任了该团体的秘书(兄弟会内部唯一的正式职位),并在 1849 年底开始编辑该团体的期刊《胚芽:诗歌、文学和艺术中对自然的思考》。该刊物于 1850 年 1 月创刊,刊载诗歌、短篇小说、散文随笔以及兄弟会特别绘制的版画。在威廉的记忆中,《胚芽》的字体是 “咄咄逼人的哥特式”,它将以月刊的形式出版,为弟兄会及其圈子追求的文化改革播下种子。最终,由于销量不佳,《胚芽》只出版了四期(1850 年 1 月、2 月、3 月和 5 月),不过,现在和当时一样,《胚芽》为我们揭示了拉斐尔前派是如何构思他们的革命工作的。[...]
拉斐尔前派兄弟会在 1849 年受到的相对平静的欢迎并没有持续下去。威廉-迈克尔(William Michael)回忆道:“[1850 年]老一辈画家和评论家们此时已经意识到,年轻艺术家们有着坚定的个人意图和一致的行动计划”。1850 年 5 月 4 日,广为流传的杂志《Ilustrated London News》揭示了 “P.R.B. ”缩写的含义,考虑到弟兄们已决定不为他们将于今年夏天展出的画作作首字母缩写,这真是讽刺。这些画作在皇家学院展出时,最受鄙视的是亨特的《一个皈依基督教的英国家庭在德鲁伊人的迫害下庇护着一位基督教传教士 》,尤其是米莱斯的《基督在他父母的房子里》。如果说前者让人感到不安,那么后者则让大多数评论家义愤填膺,因为它与三年前约翰-罗杰斯-赫伯特(John Rogers Herbert)在《我们的救世主在拿撒勒与父母在一起》(The Youth of Our Lord)中向学院成功展示的同一主题的理想化渲染大相径庭 。米莱斯的画作富含典型象征意义,人物逼真而不加修饰,对历史上圣洁家庭的贫困生活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但这幅画作仍然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这幅画引起了严厉的评论,其中一篇评论写道:“在所有(意大利原始画家)作品中,结构知识的缺乏从未造成完全的畸形。未清洗的身体所带来的令人厌恶的不便并没有以令人厌恶的现实呈现出来;肉体的污秽也没有被利用来作为一种人为的宗教情感手段来揭示低级趣味”。
尤其臭名昭著的是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写的一篇尖刻的批评文章,虽然他的作品中的人物都是现实生活中不完美的人,但他无法理解像米莱斯这样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为什么要把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混为一谈,而且还否定了艺术向理想化美发展的历史进程。猛烈的批评让兄弟会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同年,皈依天主教的詹姆斯-科林森(James Collinson)辞职。在附近的国家学院(自由学院的新名称)展出的是加布里埃尔的《Ecce Ancilla Domini》,一位评论家写道:“这幅画仅仅是对古代艺术技术的枯燥模仿--镀金的华丽、画框上奢侈的涂鸦和其他苍白荒诞的东西--这就是它的全部傲人之处”。事实上,画框上的题词是拉丁文,而拉丁文标题本身也激怒了一些公众,因为他们已经对英国天主教教权的恢复感到担忧,而这一讨论已久的事件最终于当年 9 月发生。事实上,拉斐尔前派的许多画作(包括《圣母玛利亚的少女时代》和《里恩兹》)的画布或画框都是居中的,其形式让人联想到历史上(即天主教)的祭坛画,但弟兄们虽然虔诚,却对基督教信仰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这一时期的大多数英国艺术家都回避宗教肖像画,因为他们担心宗教肖像画会带来陷阱(以及销售不佳);因此,《基督在父母家中》 和《Ecce Ancilla Domini》代表了作者的革命性尝试,即让宗教肖像画在英国重新流行起来,但又不退回到天主教的风俗中,而是强调《圣经》所提供的强烈情感和普遍的人性主题。





在 《圣母玛利亚的少女时代》和《Ecce Ancilla Domini 》中,加百列通过鲜明的效果和不同寻常的构图,令人信服地提醒新教公众圣母的普世纯洁性,为后一幅画注入了心理能量,增强了天使长带来的信息的神奇和超自然的一面。在国家机构 1850 年的展览中,与《Ecce Ancilla Domini》同时展出的还有《 第十二夜》,这是沃尔特-德维尔(Walter Deverell)所画的莎士比亚名剧中的一个场景,他当年曾申请加入兄弟会,但从未正式当选。在这一时期,莎士比亚几乎受到所有英国公民的推崇,但拉斐尔前派对吟游诗人有着特殊的热情,他们画了几段情节,强调莎士比亚作品的道德和情感深度,而不是其娱乐性(德弗内尔本人是一名演员,作为一名艺术家,他擅长莎士比亚题材)。Deverell 的画作采用了前拉斐尔派摒弃对称构图的手法,顶部以拱门为界的扁平透视让人联想到戏剧布景。虽然人们的视线首先被中心的人物(德维尔饰演的长发奥西诺、加布里埃尔饰演的小丑费斯特和伊丽莎白-西达尔饰演的维奥拉)所吸引,但并不清楚下一步该看哪里。“泰晤士报》写道,德维尔试图 ”将平淡的中世纪风格转变为更具人性的故事,但他的脸很普通,虽然他很用心,但他的举止比他的天才更明显"。无论其成员是否愿意,19 世纪 50 年代的轩然大波为拉斐尔前派兄弟会带来了声誉,以至于维多利亚女王亲自前往 《基督在他父母的房子里》,想看看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1851 年春,拉斐尔兄弟会在伦敦展出了他们的最新画作,包括米莱斯的《鸽子回到方舟》(选自《旧约全书》)和《 玛丽安娜》(选自丁尼生),以及亨特的《瓦伦丁从普罗提乌斯手中救出西尔维亚》(选自莎士比亚的《维罗纳的两位绅士》)。米莱斯的《樵夫的女儿 》于 1851 年在学院展出,这幅画以栩栩如生的方式描绘了青翠的英国风景,其自然主义的生动性和令人信服的透视效果超过了当时拉斐尔前派的任何其他作品,因此获得了更多好评。这幅画的灵感来自支持兄弟会的诗人考文垂-帕特莫尔的一首诗,画中描绘了一个富家子弟向背景中正在砍树的樵夫的女儿莫德献上一把草莓。他们的友谊会孕育出一个私生子,莫德在发疯之前会把这个孩子淹死,因为不同阶级的人之间是不可能结婚的;被砍倒的树代表莫德本人。正如在《 伊莎贝拉》中一样,米莱斯将这些社会分化表现为不道德和非人道的;这里的当代背景使批判更加明确,与卡莱尔、罗斯金和福特-马多克斯-布朗在其他背景下表达的对工人的同情相呼应。[...]
1851 年 5 月,在伦敦展览开幕后不久,罗斯金给英国主要报纸《泰晤士报》写了两封雄辩的信。他的话虽然不完全是恭维,但却改变了公众对拉斐尔前派计划的看法:“他们打算在这一点上回归过去:他们希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画出他们所看到的,或者他们推测可能是他们想要表现的场景的真实情况,而不受所有传统绘画规则的影响;他们选择了这个虽然并不不准确但却不幸的名字,正是因为这是前拉斐尔派艺术家们的做法在拉斐尔时代之前,所有艺术家都是这样做的,而在拉斐尔时代之后,他们不再这样做了,而是试图画出美丽的画作,而不是表现真实的裸体;其后果是从拉斐尔时代到今天,历史艺术处于明显的衰落状态”。
1847 年,亨特阅读了罗斯金的《现代画家》一书,并对他提出的 “以完全纯朴的心转向自然[......]不拒绝任何事物,不选择任何事物,也不鄙视任何事物;相信所有事物都是好的和公正的,并始终以真理为乐 ”的要求表示钦佩。罗斯金在给《泰晤士报》的信中将 “赤裸裸的事实 ”与自然等同起来,巧妙地将焦点 从拉斐尔前派的原始主义转移 到他们的自然主义以及他们对直接观察(而非理想化)的 执着上,提醒观察者过去与现在并非水火不容。相反,他指出,拉斐尔前派 “并不打算放弃现在的知识或发明可能为他们的艺术带来的任何好处”。罗斯金的支持为兄弟会打开了许多视野和大门;然而,早在 1850 年 12 月,威廉-迈克尔就注意到兄弟会正在逐渐解散。这在前卫艺术的发展史上屡见不鲜,显然兄弟会对于米莱斯、亨特和罗塞蒂来说已经失去了作用,他们正朝着不同的方向迅速发展。在短暂的相处中,他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揭示了新的美学可能性,其回声至今仍在回荡。1850 年 8 月,一位评论家在《卫报》上评论道:“迄今为止,英国艺术家都是各自为战,实际上没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也没有一个恒定追求的明确思想目标[......]在这里,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学校[......]它的目标[......]是崇高而纯粹的。走在我们的街道上,没有人会不注意到我们现在的品味是多么堕落和物质化[......]。他们的努力取得成功将是国家之福”。兄弟会掀起了一场’国家之福’的起义,这场起义生根发芽,至今仍在继续。
免责声明:本篇意大利语原文的中文翻译由自动工具生成。 我们承诺会对所有文章进行审核,但无法保证完全避免因软件造成的翻译误差。 您可以点击 ITA 按钮查看原文。如发现任何错误,请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