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空虚,由我们选择不成为的一切组成,由我们出于恐惧、出于惰性、出于生存而留下的所有版本组成。这种空虚并不猛烈地表现出来,而是像一种微妙的、难以察觉的疼痛一样悄然袭来,它知道该从哪里下手,在哪里挖掘,在哪里病态地翻找。它是由充满无言言语的夜晚、与那些无法理解我们的人共处的房间、甚至还没有名字就被打断的爱情组成的。它是一种缺失,即使我们没有说出它的名字,它也会让我们保持清醒,它在最平淡的细节中回归:一盏灯的亮起、一段画外音、一段永远不属于我们的记忆。
还有另一种更稀有、更脆弱的虚无,它不是惩罚而是欢迎,不是伤害而是安慰。是它让我们不再伪装,是它让我们在虚弱的瞬间,保持毫无防备的状态。它不是要求,而是提供:它邀请我们停下来,呼吸,成为虚无,并在虚无中最终成为存在。宇宙空间的虚无:恒星之间的绝对寂静。还有亚原子粒子的虚无,它将万物联系在一起。但是,存在的虚无才是最难维持的,我们试图用语言、手势、图像、背景噪音和嗜好来填补它。我们加快步伐,心不在焉,疲于奔命,但虚无依然存在,它伴随着我们,隐藏在缝隙之间,迟早会追上我们,因为它的呼吸永远比我们的长。
精神病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曾经说过,人不能没有意义地活着,而因意义缺失而产生的空虚会成为一个无声的、毁灭性的陷阱。他称这种空虚为 “存在的空虚”,因为当我们不再感觉到 “为什么”,不再感觉到我们的存在与我们的所作所为之间的联系时,这种空虚就会慢慢消失。他在纳粹集中营中直接而残酷地体验到了这一点,这也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人对意义的探索》的核心内容。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达豪集中营和其他集中营服刑期间,弗兰克尔失去了怀孕的妻子、父母和兄弟,经历了姓名、身体、自由和未来的完全剥夺。在那种绝对的空虚中,人类似乎被消灭了,弗兰克尔观察到了一些根本性的东西;那就是,即使在最极端的苦难中,人也保留着一种内在的自由,那就是在面对痛苦时选择自己的态度。"人的一切都可以被剥夺,但有一样东西除外:人类最后的自由--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选择自己的态度,哪怕只有几秒钟。
在弗兰克尔看来,存在的空虚不仅仅是一种现代心理状态,而是一个关系到意义可能性的领域,正是在一切都崩溃的时候,人类才有机会问自己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为什么活着?为了什么而反抗?在弗兰克尔看来,答案并非来自外部,而是一种积极的建构,是每个人都必须产生的一种取向。只要我们停止恐惧,开始将其视为一种可能,那看似无法忍受的空虚就会变成一个可以居住的空间。拯救我们的不是充实,而是将缺失转化为方向,将迷失转化为定位的能力。我们经常犯的错误也许就是从不给它空间。我们害怕空虚,仿佛它是我们生活结构中的一个缺陷,是一个需要纠正的错误,甚至在艺术、音乐、写作中,每一个表面都必须是饱满的,每一个音符都是连续的,每一个短语都是不间断的串联。因为沉默是入侵者,是中断的不适,是空白画布的对手。但是,如果我们不再与它抗争,不再与这种看似撕裂而又乏味的空虚抗争,而只是学会栖息于它,照顾它,我们就会明白,它不过是词语之前的呼吸,手势之前的等待,画布依然完好无损。它是一个节拍和下一个节拍之间的必要停顿。它是想象力、创造力的沃土,也是理解我们无法理解的一切的沃土。虚空不仅是缺失的东西,也是仍然可以诞生的东西。但空虚不会被填补。它被倾听。它是有人居住的。在这个催促我们不要停歇的时代,栖息于虚无似乎是一种激进的行为;它意味着停留、倾听、抵制人类渴望饱和的强烈诱惑,并简单地接受这样的事实:在充实与虚无之间不确定的临界点上,有些事情无法真正发生。
罗伯特-雷曼(Robert Ryman)选择白色,不是为了否定,而是为了肯定,他准确地理解了这一点。他的画,不是表现,而是揭示;不是呐喊,而是坚守。在他的作品中,光线沉淀,边缘消失,墙壁不再是背景,而是成为作品的一部分。20 世纪 60 年代末,雷曼的作品出现了感性的转变:他的作品表面变得轻盈、半透明,几乎不确定。在 1966 年的《双子》和 1967 年的《阿德尔菲》等作品中,白色颜料薄薄地铺展开来,紧贴着支撑物的最边缘,似乎在试图容纳虚空,但又不将其包裹起来。在《阿德尔菲》中,画布甚至没有拉伸,而是松散地放在蜡纸上,并直接钉在墙上。正是在这种姿态下,雷曼开始将墙壁浪漫化,将画框作为画作的一部分,模糊了艺术与空间之间的界限。但在 1970 年的《表面面纱》系列中,这种反思被放大了,他在玻璃纤维或涂油的纸张上绘制了难以捉摸的表面,并用胶带短条固定在墙上。支撑物和环境之间不再有任何距离:墙壁进入作品,成为其表皮,看着这些作品,很难理解绘画在哪里结束,墙壁在哪里开始,材料在哪里溶解,在哪里成为存在。在这里,白色不是完全的光,而是雾气、悬浮物、潜伏物。雷曼仿佛在要求我们停留在那里,停留在意义尚未确定的确切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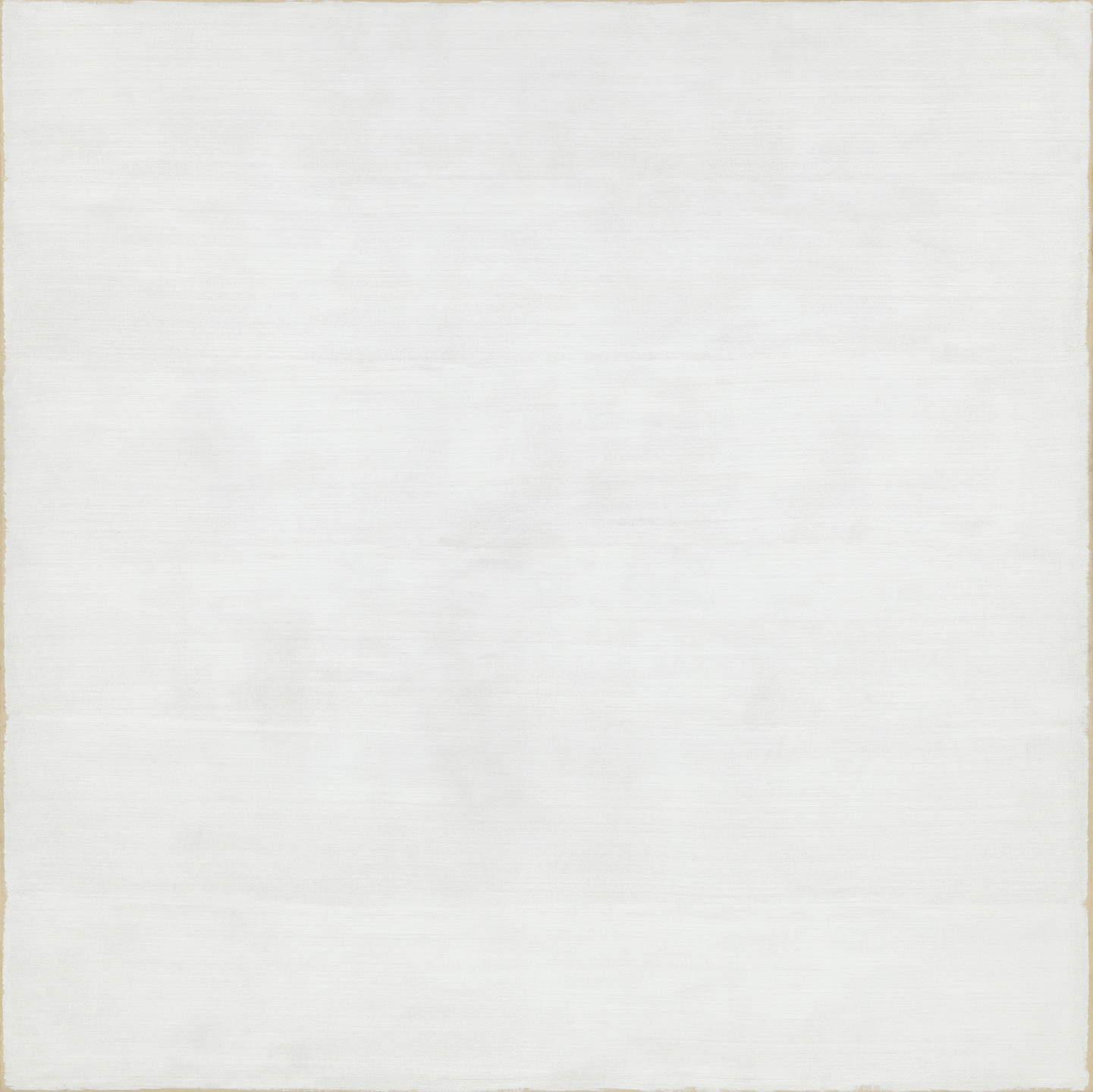

他说:“我的画作与墙壁的关系如此密切,有时几乎就像画在墙上一样。”我认为,正是在这个门槛上,在存在与不存在之间的缝隙中,他的作品找到了真正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肯定,而是暗示,是等待。与罗伯特-雷曼的作品一样,在保罗-索伦蒂诺的《这是上帝之手》中,缺失既不是装饰,也不是缺乏,而是存在与可能存在之间的张力。雷曼将白色作为一个栖息的空间,让人心无旁骛地通过;而索伦蒂诺则让沉默成形,成为叙事的实质。影片中有些时刻,音乐完全消失,声音消失,只剩下一个比任何对白都要沉重的声音深渊。这同样是失去后的空虚,是创伤后残留的撕裂感。在主人公家中的寂静中,父母的离去不是被言说,而是被感知。哀悼不是说教式的,而是悬浮的、残酷的、真实的。与雷曼的白色作品一样,索伦蒂诺的作品也是轻盈的,几乎是非物质化的画布,他让缺席成为一个可以穿越的视觉和情感领域,但最能让空虚成为一种真实语言的艺术家或许是作曲家约翰-凯奇。
1951 年,约翰-凯奇进入一间消声室,他深信自己会遇到绝对的寂静,但他得到的却是一个残酷而冰冷的事实,即寂静并不存在。
在这个旨在吸收所有声音的房间里,他听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一种是他的心脏跳动声,低沉而有规律;另一种是他的神经系统运作声,发出的声音更大、更连续。那一刻,他意识到,即使万籁俱寂,身体也会说话,现实没有完美的真空。每个空间都有人居住。每一个期待都是噪音。
4’33" 是他最著名、最受人关注的作品:4 分33 秒的 “演奏 ”寂静,演奏者从未接触过乐器,但空旷却从不乏味。他的聆听时间只需要一个人去关注,停止控制声音,接受已经存在的东西。4’33" 有乐谱、有节奏、有框架。结构是存在的,但填充它的东西是不可预知的,在这种明显的缺失中,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观众的咳嗽声、大厅的嘈杂声,甚至仅仅是自己的呼吸声。
凯奇在《沉默:演讲与写作》一书中写道:“无论我们身在何处,我们听到的大多是噪音。当我们忽视它时,它扰乱了我们。当我们倾听它时,我们会发现它的魅力”。也许正是这一点赋予了这部作品更多的意识:即使我们发现周围空无一物,它依然存在,依然存在。然而,这部至今仍令人不安、恼怒和感动的作品并非凭空出现,也不是为了挑衅而挑衅。凯奇自己也说过,是罗伯特-劳申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的例子给了他创作这部作品的勇气(或许是必要):当他第一次看到他 1951 年的《白色绘画》(White Paintings),那些以完全白色的网格排列的单色油画时,他意识到音乐也必须跟上时代,接受艺术的激进邀请,停止填充。
白色油画 既没有图像也没有内容,但同时又是空洞的表面,只是在表面上,随时准备迎接反射、阴影和存在。它们什么也不代表,却欢迎一切。它们是关注的空间,当有人从它们面前经过时,在光线的变化中,在空气微不可察的流动中,它们就被激活了,凯奇在这些画作中认识到了一个他再也无法忽视的门槛。"凯奇在《沉默》一书中写道:"对任何人来说:白色画作在先;我的无声作品在后。演讲和著作。4’33 "成为那些白色画作的一种声音转译,是一个可以不假思索地栖息的空间,一个不被主宰的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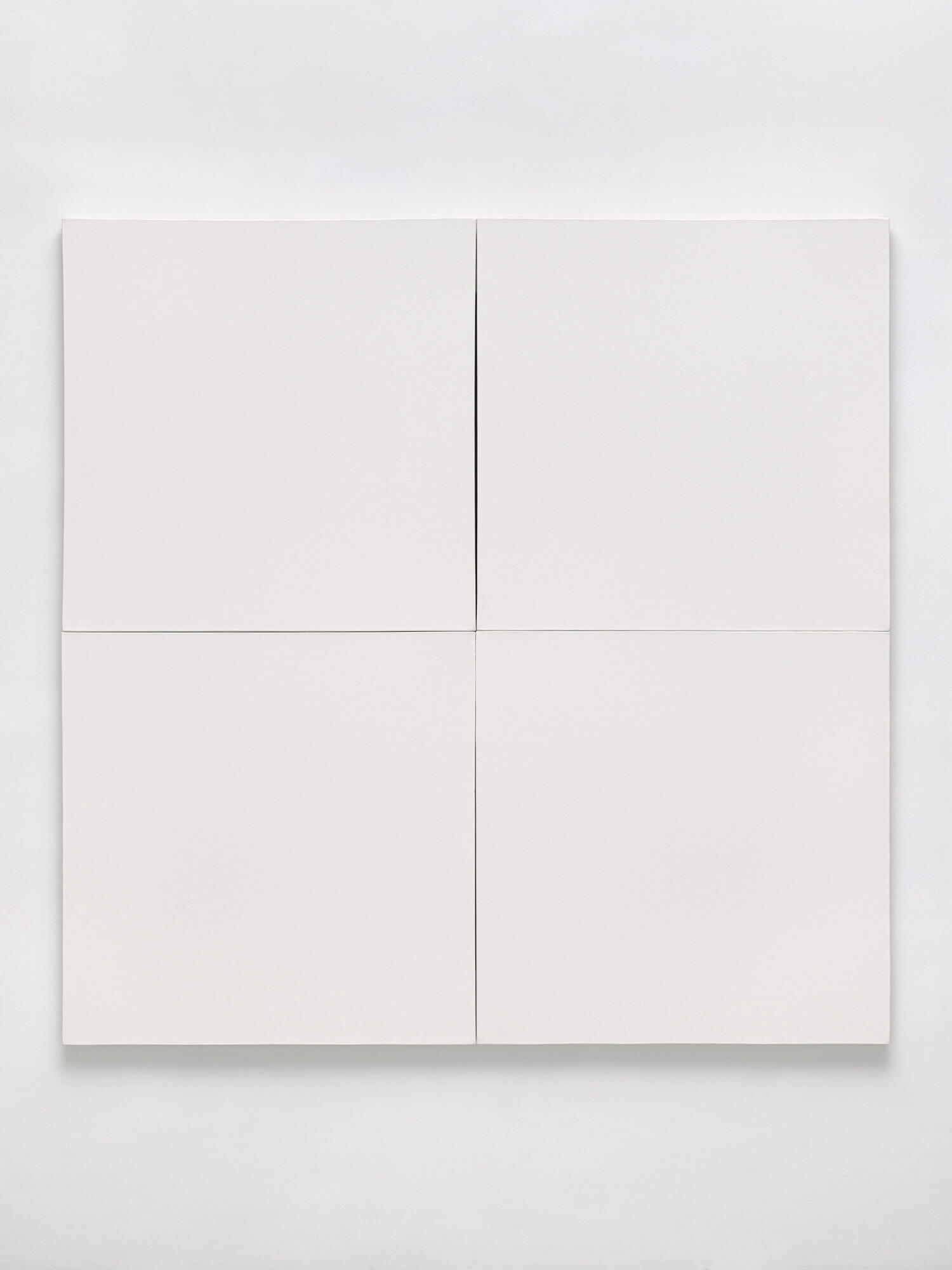
在另一个时代,另一种语言也能为同样的震颤命名。在《约伯记》中,人类发现自己赤身裸体地面对无法解释或填补的缺失:“但是,看哪,如果我去东方,他不在那里;如果去西方,我找不到他;如果去北方,当他在那里工作时,我看不到他;他藏在南方,我看不到他”。约伯从各个方向寻找上帝,但都没有找到,毁灭他的不是黑暗,而是被隐藏的存在,是撕心裂肺的寂静。事实上,伤害约伯的不是上帝的缺席,而是他无法看到上帝的存在:“因此,在他面前,我惶恐不安;一想到他,我就害怕”。让人害怕的不是黑暗,而是在没有答案时敞开的广阔,是无形的充实,它暴露了我们,解除了我们的武装,提醒我们有些东西在我们之外。
在约伯求而不得的地方,西奥兰明确地打开了深渊,它不再是一个可以栖息的空间,也不再是一个可以理解的期待,而是一种腐蚀、一种不完整、一种不存在的地方,在那里,每一个字都有崩溃的危险。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位介于哲学家和私人思想家之间的人恰恰选择了与文字抗争。在《解构要略》中,箴言变成了薄薄的刀片,形式简化为骨头,美学屈从于直觉。在西奥兰看来,空虚是每一种思想的终极命运,是思想的盲点,在这里找不到任何慰藉或救赎的可能,但这正是它的魅力所在:能够抵御意义的诱惑。“存在意味着利用我们的那部分不现实,意味着与我们内心的空虚相接触而振动”。
在西奥兰那里,意义的危机既不是隐喻,也不是美学,而是当其他一切都衰败时唯一幸存的现实,因此空虚成为一种极端的清醒,但这种清醒是内爆的,是放弃自身的。没有禁欲主义,没有等待。只有残留。这是一种缺失,他的缺失,它什么也没有宣布,却揭示了存在的不可能性。这里潜藏着一种微妙而有害的诱惑:将空虚转化为存在本身的代名词,将空虚伪装成意义,将不属于空虚的功能赋予空虚。但是,这样做会背叛它,扭曲它。因为虚无生来就不是为了安慰,也不是为了提供立足点,因为它的根本使命是超脱、彻底的悬置、非存在。于是,一个也许是最隐蔽的问题出现了:如何坚持空性,而不让自己被空性所诱惑?如何保持在它的轨道上,而不把自己投射到欲望之中,不给它加上虚无本身本质上并不追求的意义?
在西奥兰的思想中,虚无也剥离了自身的负面特质:它不是作为一种威胁的虚无,而是作为一种清晰而不可阻挡的残留,作为一种不再需要的现实,一种没有眩晕的深渊,一种干燥、尖锐、外科手术式的、近乎冷漠的确定性,它不是将我们连根拔起,而是将我们掏空,只留给我们本质,即对我们的非现实性的认识。海德格尔警告我们:当我们问 “虚无是什么?”时,我们已经把它当作一个实体来对待,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背叛了它的本质。虚无不是某物,而是我们无法拥有、也无法转化为对象的不可还原的空间。在《存在与时间》第 40 段中,海德格尔分析了 “痛苦 ”的基本情感状况,并将其与 “恐惧 ”区分开来。后者有一个对象,而痛苦没有,它不可定位,不是 “属于 ”某物,它是一种感知,即我们所知道的世界可能会在我们脚下坍塌,就在那一刻,“虚无 ”和 “无处 ”显现出来,所有的确定性突然中止。世界并没有消失,而是失去了意义,原本熟悉的一切突然变得陌生。在这一视野中,内疚不是一种道德错误,而是一种本体论形式:存在之所以有罪,是因为它是虚无的基础,是因为它被抛入了一个它未曾选择、但无论如何都必须居住的存在之中,死亡不是作为事件的终结,而是存在的纯粹、简单、精致的不可能性的可能性。在这种彻底的、不可还原的可能性中,人类被要求决定成为他自己,把自己的虚无作为一个起点,而不是一种谴责。对海德格尔而言,虚无不是虚无主义,不是本体论的缺乏或价值的缺失,不是缺陷,而是存在的变化结构。这种 “非 ”不是剥夺,而是让存在的脆弱和真实变得可见。
在日本,这种 “空 ”被称为 “间”(Ma),它不是缺失,而是连接。它是手势之间无形的边缘,是言语之间无声的回响,是一个呼吸结束和另一个呼吸开始的微小空间。在马氏看来,这不是缺陷而是节奏,不是悬浮而是形式,正是这种微妙的张力让意义得以显现,让相遇得以发生和呼吸。吉田谦光在《闲暇时光》中也反思了不完美和短暂事物的无声魅力。他指出:“虚空总是包含着事物,”这似乎在提醒我们,打动我们的永远不是完美,而是消失前那非常脆弱的瞬间,就像一片被时间荡漾的树叶、一个碎裂的碗、一个残留的碎片。长谷川登鹤的《正林祖 byōbu》中也有同样的悬念,这幅由六幅画组成的作品展现的不是风景,而是风景的残骸。松树从浓雾中浮现,没有强加于人,它们是犹豫不决的存在,沉浸在一片寂静中,而不是沉默,而是倾听。
这幅 “屏风”(画在纸上的屏风,用丝绸镶边,裱在漆结构上)不是用来悬挂的,而是用来栖息空间、修饰空间、设计空间节奏的,它最初的功能不是艺术,而是建筑。在日本,艺术与生活从不分离,事实上,“画室 ”的陈设、分割、打开都十分精致,其设计目的是调节光线,陪伴人们的视线。


在《正林祖 byōbu 》中,没有叙事,没有中心,只有持续的悬浮,一种静止的邀请。因此,东伯只是通过提供一个停顿的空间来描绘间隔。我们不是在完整的事物中认识到自己,而是在那些逃避、颤抖、抗拒而又不宣示自己的事物中认识到自己,因为事物在即将消逝时才会发出最响亮的声音,也许正是在那里,它们才最像我们。它不回应,不安慰,不为我们提供救赎,但它注视着我们,在它沉默的目光中,让我们恢复自我。它不是缺席的形式,而是开始的形式,它不会让自己被占有,但可以被倾听,也不会被跨越:它保持着,悬浮着,就像我们可以栖息一样。
因为栖息于虚无意味着接受自己没有答案,不理解一切,不一定要治愈。这是一种既简单又激烈的姿态:即使一切似乎都不存在,也要保持存在。在这种不言而喻的脆弱中,也许会发生最真实的事情,那就是认识到存在不是为了占有,而是为了停留。它不是填补,而是守护。它不是认知,而是感受。因为如果空虚是存在的条件,那么它就不仅仅是缺乏,而是基质。它不是万物消融后的残留,而是万物的起点。

本文作者 : Francesca Anita Gigli
Francesca Anita Gigli, nata nel 1995, è giornalista e content creator. Collabora con Finestre sull’Arte dal 2022, realizzando articoli per l’edizione online e cartacea. È autrice e voce di Oltre la tela, podcast realizzato con Cubo Unipol, e di Intelligenza Reale, prodotto da Gli Ascoltabili. Dal 2021 porta avanti Likeitalians, progetto attraverso cui racconta l’arte sui social, collaborando con istituzioni e realtà culturali come Palazzo Martinengo, Silvana Editoriale e Ares Torino. Oltre all’attività online, organizza eventi culturali e laboratori didattici nelle scuole. Ha partecipato come speaker a talk divulgativi per enti pubblici, tra cui il Fermento Festival di Urgnano e più volte all’Università di Foggia. È docente di Social Media Marketing e linguaggi dell’arte contemporanea per la grafica.免责声明:本篇意大利语原文的中文翻译由自动工具生成。 我们承诺会对所有文章进行审核,但无法保证完全避免因软件造成的翻译误差。 您可以点击 ITA 按钮查看原文。如发现任何错误,请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