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尔路易吉-弗莱西亚(1962 年出生于阿斯蒂)在皮诺-托里内塞(都灵)生活和工作。他的艺术研究始终属于概念领域,通过不同的媒介--从绘画到录像,从摄影到文字使用--进行发展,通常以多媒体的方式进行组合。自 1993 年以来,他定期在意大利国内外举办展览,并在都灵 Galleria Martano、米兰 Galleria Milano、热那亚 Vision QuesT 4rosso、博洛尼亚 Studio G7 和佛罗伦萨 Galleria Il Ponte 等重要场所多次举办个展。最近的作品包括L’impotenza celeste deipianeti》(佛罗伦萨 Il Ponte 画廊,2025 年)、《Di sola andata》(都灵 Riccardo Costantini 画廊,2023 年)、《ANTOLOGICA》(因斯布鲁克,2021 年)、《La velocità della luce》(布雷西亚,2021 年)。他的作品曾多次参加大型国际当代艺术博览会,包括马德里艺术博览会(ARCO Madrid)、都灵艺术博览会(Artissima Turin)、博洛尼亚艺术博览会(Artefiera Bologna)、Arteverona、米兰国际艺术博览会(MIA)和米兰米亚特博览会(Miart Milan)、巴塞尔摄影博览会(Photo Basel)和欧洲摄影博览会(Fotografia Europea)(2010 年、2015 年)。他还参加了古比奥雕塑双年展(2006 年)和韩国大邱摄影双年展。他的作品被重要的公共和私人收藏,包括都灵 GAM、罗韦雷托 MART 和纽约 MET。他曾多次参加在机构空间和画廊举办的群展,包括Il tempo della comunanza(萨卢佐,2024 年)、The Family of the Man(奥斯塔,2021 年)和Under The Lucky Star(热那亚,2012 年)。在与加布里埃莱-兰迪(Gabriele Landi)的对话中,皮埃尔路易吉-弗莱西亚向我们讲述了他的艺术创作理念。

GL.让我们从头开始,一个无意识的开始,对许多人来说,这与童年不谋而合。
PF.通常,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你总会回到那个时刻。当然,当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你并不知道什么是艺术,你只是感觉到有一种想去做的冲动。而我,在那个年纪,手里总是拿着铅笔或画笔,我必须做点什么:画画。这是一种表达自我的冲动,而这种渠道似乎是最自然、最可行的。事实上,在某些方面,它甚至超过了语言。当然,我并不是失语症患者,但我能用绘画更好地表达和解决我的争论。虽然绘画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词,但它仍然是最适合我的表达方式。至于我是否真的能用这种方式完全表达自己,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你从这里开始,然后慢慢意识到这是一件具体的事情。你和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不同,这是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就像那些对音乐有一双耳朵的人,或者有跳舞或做运动的能力的人一样。当然,我是在一个小镇上长大的,所以并不容易。我不想把我的这段生活浪漫化:我的家庭很普通,我的父母没有受过教育,但他们总是让我做自己,从不妨碍我。对此,我至今仍心存感激。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紧迫感是否也指导了你的学校选择?
完全没有。事实上,这是唯一有点问题的地方。我住在阿斯蒂省,那里没有艺术学校。尽管老师们坚持对我的父母说:’这个孩子必须去上艺术学校’,但我十三岁半就每天去都灵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可能的。于是我做出了另一个选择,但我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没有放弃。我一直在学习,做自己的事情。高中毕业后,我进入艺术系学习,尽管我从未完成学业。我从小就跟着村里的一位画家学画画,他是一位在比赛中获奖的画家。我小时候也参加过一些比赛;就在我跟你说话的时候,在我画室的旁边有一个奖牌柜,里面装满了那些年获得的奖牌。是的,这些奖牌是鼓励你的东西,是看到绘画、雕塑作品的一种方式,简而言之,是看到那些充满激情的艺术家的作品,即使他们是业余爱好者,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蒙费拉托小镇,这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因此,我经常在乡村节日期间举办的业余画展上看到他们的作品,包括比武和其他活动;而在一年的其他时间里,我则在教区教堂里欣赏壁画。在我家,除了买来装饰用的几幅版画外,没有任何艺术品。后来我开始看我哥哥的书,他在中学从事艺术教育,于是我开始了解自己,开始阅读,然后从图书馆借书,幸运的是,村里提供图文并茂的专著和艺术史书籍。总之,就是这样。
您有过艺术初恋吗?有没有什么东西特别激发了你的想象力或兴趣?
我也说不清楚。我们追溯的时间太久远了,很难确定一个准确的起点。我的起点更多的是出于身体需要,想用双手做些事情。一开始,我主要画我看到的风景、狗、猫以及我眼前的事物。最让我烦恼的事情是临摹。我有一些朋友临摹别人或书本上的画,这让我很恼火。这并不是因为我认为自己画得好,或许我天真地认为自己画得好,毕竟孩子都是自负的,但他们应该自负,因为他们必须要求自己做到最好,才能进入外面的世界并迈出第一步。然而,现在回想起来,我确实记得一些....我记得,我母亲是一位裁缝,她的顾客中有一位波兰女士,她是一位难民(冷战是一个具体的现实),年轻时曾在华沙学习过艺术。当她来找我母亲买衣服时,她会看到我在角落里画画,我记得她说:’啊,这个孩子有一只手!’。当时,我母亲认识一位业余画家,我和她关系很好,她现在还活着,名叫蒙娜丽莎,这个名字很有保障!她画的是风景画,我必须说,她的画也非常美,她受到印象派画家的启发,在色彩的选择上有很高的品味。她的画都是极好的风景画,还有一些静物画;因此,我母亲把我送到她那里去学习。那时我八岁,也许九岁。正是她,蒙娜丽莎,教会了我如何使用油画颜料,而我却不知道。我父母给我买了油画颜料、调色板和一个小画架。我几乎每天下午都去她家画画,因为我住在山上,所以要走 5-6 公里。时不时地,她会拿起我的画笔,纠正我的画,我承认这让我很烦恼。他会说:’不行,要这样画’。我当时又害羞又茫然,我至今还记得她对我说这句话时房间里的光景:这是灵魂深处的脚印,一直在那里追寻着一条路。我和这位女士的关系一直很好,我爱她,她向我揭示了油彩的秘密,如何混合、稀释、涂抹,然后是松节油的芬芳,美妙的回忆。那香味现在还在,很美,能让你进入状态,让你立刻觉得自己是个画家。诶,这就是开始,正如你现在意识到的,是作为一个画家的开始。









您已经暗示过您在绘画和素描之间的来来往往......
我认为绘画是人类最古老、最神秘的表达方式之一。它能够留下痕迹,然后变成文字、信息或图形,这并不重要。对史前人类来说,用手指在沙地上描画就已经开始了一场变革,一场巨大的变革。这是一种觉悟的姿态,一种对自身存在的觉悟:是你作为一个个体画出了这个符号,是你创造了它,你以你希望的方式创造了它,让一些以前不存在的东西显现出来,由于这种姿态,它显现了自身,也显现了你自己。
绘画也出现在你现在的作品中,是吗?
是的,当然。即使在我目前的作品中,我主要使用摄影,但构图总是从绘画构思开始。它确定了获得我心目中图像所需的空间布局。即使在拍摄之前,我也要考虑到周围的元素,在头脑中想象出我想要的东西。我不认为自己是严格意义上的摄影师。例如,我不是卡蒂埃-布列松式的街头摄影师,我不是寻找决定性瞬间的人--假设这一切并非事先计划好的,但让我们假装它是计划好的。我不喜欢捕捉完美的、出乎意料的瞬间,也不喜欢捕捉出乎意料的顿悟。这种方式意味着完全沉浸于生活的洪流之中,与社会及其所提供的一切直接互动,在那里找到可以创作的主题和素材。不,这不是我的风格。这也是因为我的作品经常涉及到人,而我并不拍摄他们。有时我会画他们或给他们画画,但那是不同的。所以,我最大限度地尊重这类作品,真的,有些美丽的东西我非常欣赏。但这是另一回事。
您刚才提到您曾就读于艺术学院。你的作品中经常,或者更确切地说,总是出现文字。您是如何在文字下面或旁边创建一个与图像的短路?
可以说这是一个诗意的想法,但也是一个漫长过程的结果。事实上,当我开始创作时,文字和图像之间并没有预先设定的联系。这是一项比想象中更漫长、更复杂的工作。例如,就在不久前,当我在等待你的电话时,我正在创作一幅图像,并将我早已准备好的文字与之相连,这些文字并不是专门为该图像设计的。有时是两年前写的,有时是两星期前写的,有时是前一天写的。然后,我开始将图像和文字联系起来,一个新的创作开始了,文字在保留其含义的同时,还必须在内容之外找到与图像的空间对应关系。随后,我开始分析文字与图像的关系。我经常意识到,在无意识的层面上,很容易将文字与特定的图像相匹配,然后意识到它变成了纯粹的标题;然后我们又重新开始。我尽量避免将文字与图像联系起来,否则一切都会坍塌。文字不是解释,不是叙述,如果没有图像的帮助,人们就无法理解,反之亦然。相反,它们是作品中必须共存和合作的两种语言形式,但每种形式都绝对保持在自己的语义和本体论轨道上。我试图产生一种迷失感,我希望激发观察者的一种全新的心理联系,引导他通过我所不知道的诠释学路径找到自己的意义。因此,如果两个实体--文字和图像--没有直接的、可验证的概念联系,观察者就会发现自己被这种认知障碍所驱使,不断尝试,以便得出某种有自己的、至少是明显的逻辑联系。例如,现在我面前有一张两棵树的图片,上面附有我写的一句话;这不一定是最终版本,谁知道呢。一旦完成,当第一次看到它的人,由于我前面提到的原因,触发了一个故事的开端,一个我完全被排除在外和不知道的叙述时,它的真正完整性才会出现。我喜欢这种想法,它让我觉得自己是观赏者的合作者。我喜欢这种感觉,它让我觉得自己是观赏者的合作者。观赏者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观察者,他可以吸收摆在他面前的一切。因此,从本质上讲,这就是艺术的根本目的,在我看来,也是艺术的主要意义:一种工具,一种引人思考、推理的邀请。只要有东西让我们思考,我们就可以认为自己是安全的、自由的;当我们停止思考时,我们就真的进入了一个没有出口的隧道。近年来的一切,从媒体到政治,似乎都在致力于将我们推向那个深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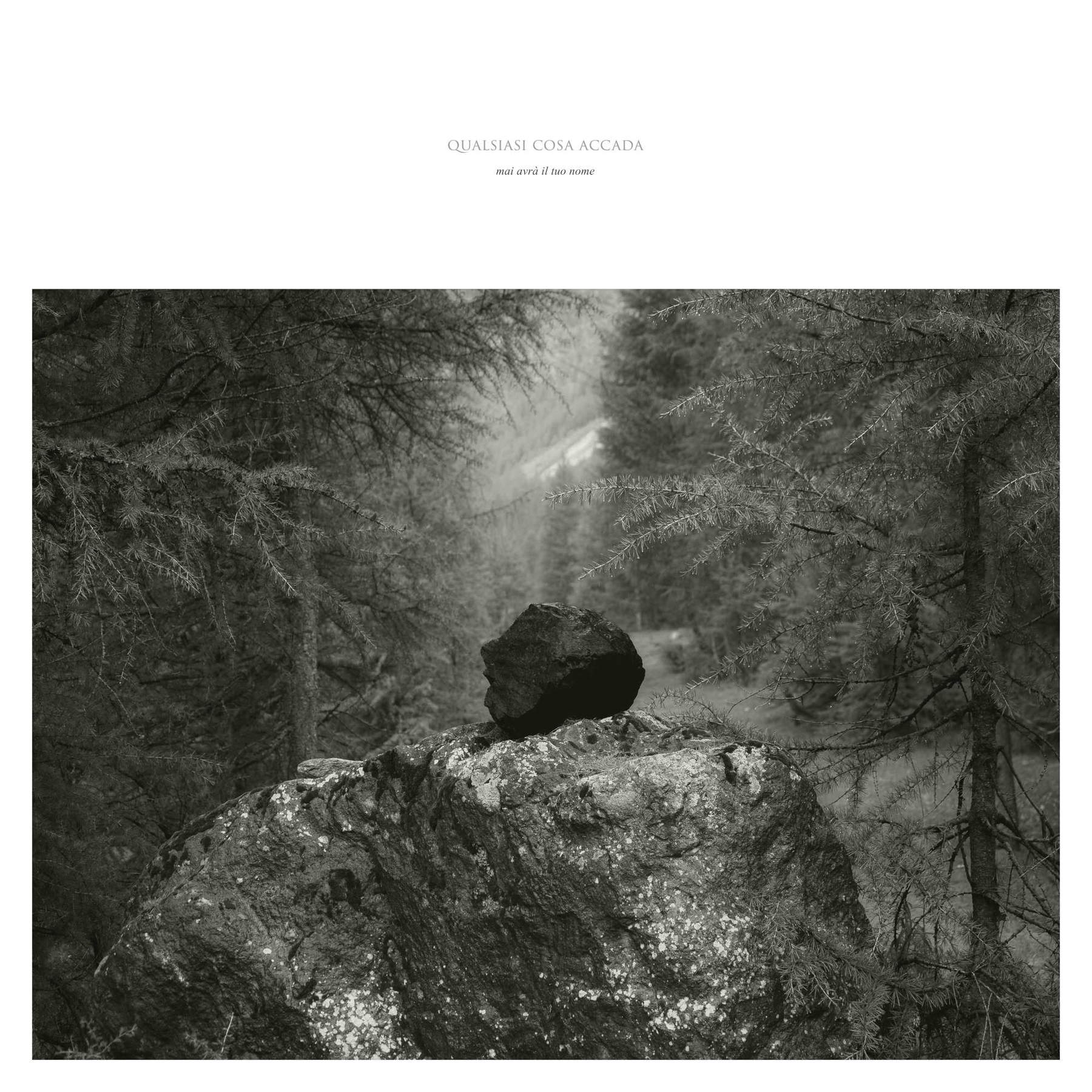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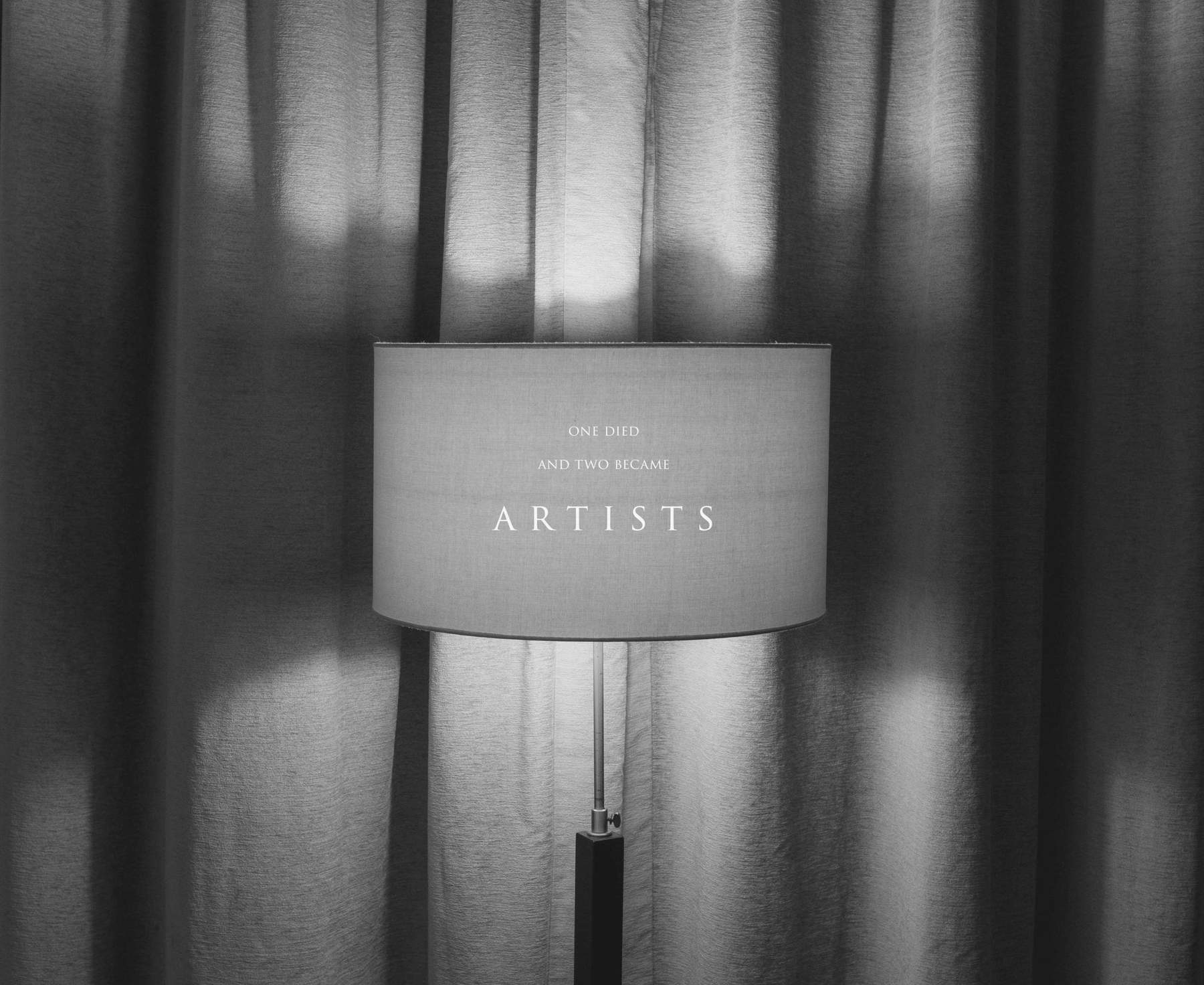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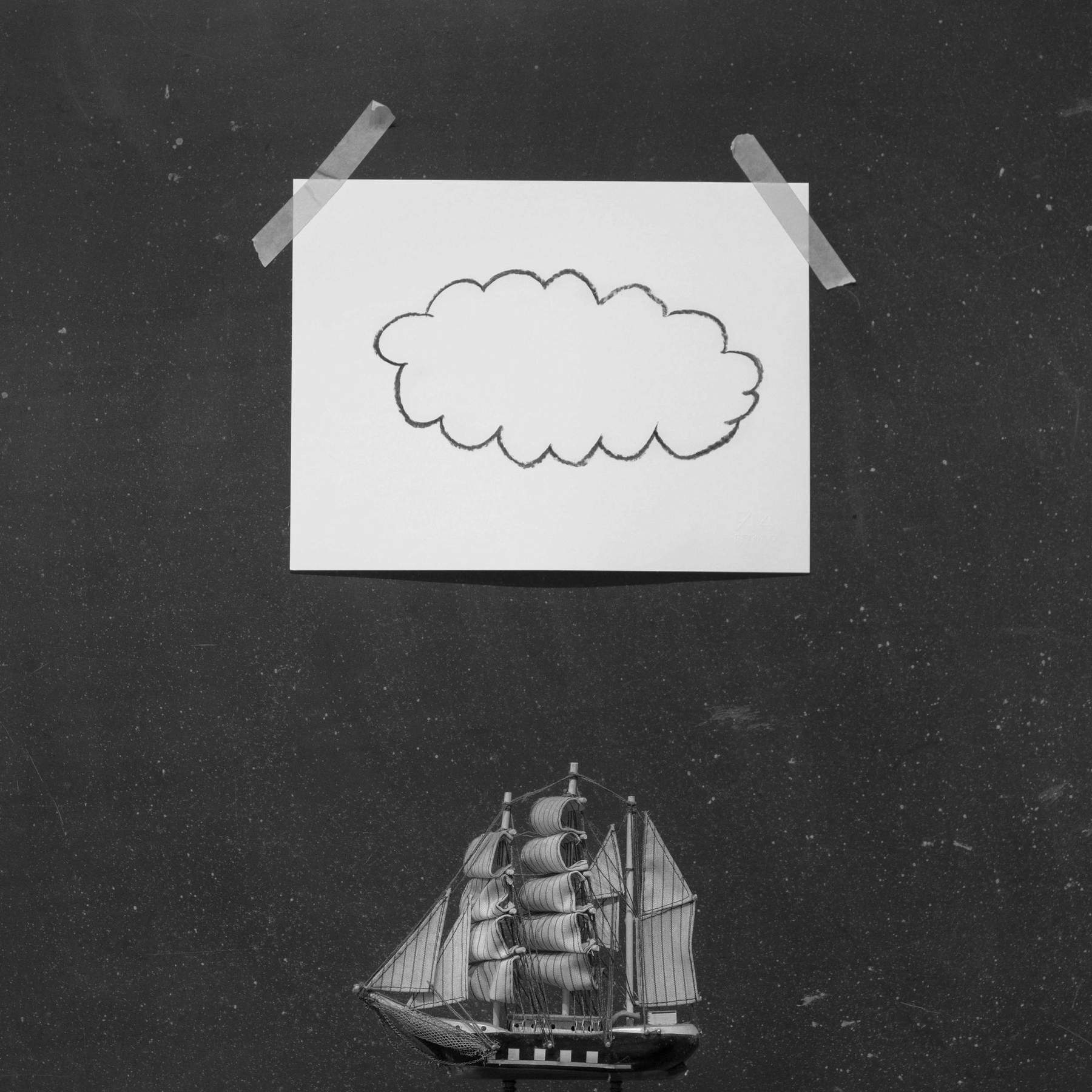
您的话让我想起了深受超现实主义者喜爱的劳特雷蒙的名言:“就像缝纫机和手术台上的雨伞偶然相遇一样美丽”。
完全正确。我认为超现实主义不是从图像的角度出发,而是从机制的角度出发。在我的作品中,这种机制不能是无意义的、纯粹的超现实,因而也不能是封闭的。我感兴趣的是,观众能在图像和文字之间形成的短路中找到自己的空间,将这一短路带到自己身边,使其成为现实的东西,或者即使不是现实的,至少也是可以想象的,从而引发想象。这样,一种 “力的关系 ”就在图像和文本之间产生了,也就是说,这种 “力的关系 ”不能理解为搏斗,但无论如何,这种关系即使在引导它的过程中无法辨认,也能以某种方式被感知,我后来意识到这是一种私人的、个人的事情,可能也源于图像和文本的积累。当然,这两样东西各自积聚在一个独立的容器中,因此有些图像会留在那里。我既摄影又写作,但从不同时进行。例如,这两棵树的图像是我现在拍摄的,但我现在要插入的句子是沿着另一条路径,来自另一个时间。比方说,当我外出拍摄,甚至在工作室里拍摄时,那种心理因素就会发挥作用,让你爱上那张图片,而不是另一张。很多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有些东西让你着迷,但你却不知道为什么。你一定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不知道,你到了一个地方,尤其是风景区,你会觉得那个地方在对你说话。就好像那个地方拥有一个矩阵,你可以在其中安放你的精神、你的存在,而这两样东西是相匹配的。在那一刻,也只有在那一刻,才是真相;如果你在下午或另一天再看到它,它就不起作用了,那里什么也没有。即使不知道究竟失去了什么,我认为不知道也是好的。也许--至少你是这么认为的--有些东西与无意识有关,与童年有关,是你第一次在那种光线、环境和感觉下看到的,然后你就创造了触发点。这就像测距仪对焦一样,两个相同的图像必须匹配、重叠、合二为一,成为一个真实的东西,然后在时间的长河中消失。有时,我曾无数次地走过某物或某地,过了一段时间才意识到那里有重要的东西,尽管我并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经常在某个地方看到一些你自以为了如指掌的东西,但有一天你却偶然看到了一些你从未见过的东西。或者,你看到它们是因为你从相反的方向走了同一条路。因此,当你看到不同的事物时,你也会想到不同的事物,然后,如果你愿意的话,所有这些事物都是联系在一起的。这让人想起您作品中的一个隐形主角:时间。
当然。我无法真正忽视时间,不是因为我决定这样做,而是因为我有这种感觉。毕竟,我们的存在完全基于事物的时间性、有限性和顿悟性。时间是我选择使用摄影媒介的主要原因之一:它由时间和光线构成。说到摄影,我觉得它非常虚假,比绘画和素描更假。它是最具欺骗性的媒介。让我们回到眼前的这两棵树:它们不是我种的,也不是我找的。它们就在那里,在乡村的某个地方。我给它们拍了照,但它们再也不会像原来那样了。只需要一阵风,或者背景中的薄雾发生变化。说照片 “捕捉 ”是老生常谈:照片什么也捕捉不到,照片失去了一切。我总是把照片比作奥菲斯回头看欧律狄刻从冥界出来时的情景:当他看到她的那一刻,他就失去了她。拍照时也是一样:你失去了她。然而,这种 “失去 ”自有其魅力。这是你留下的影像--纸质的仿真、数字的或任何你想称之为它的东西--不再是,或还不是,或也许会再次成为,谁知道呢。但每当我看到它,那东西又’是’了。因此,图像成了你个人 “包袱 ”的一部分,成了你内心原型图像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我几乎可以说这是一种怀旧,怀念你所喜爱但又无法再辨认的东西,所以你重新创造它,以便留下痕迹,成为一种对话和解释自己的字母表。
前段时间,我记得我曾请你谈谈你与工作室之间的关系,你给我发了一系列图片,这些图片以某种方式展示了一些与档案有很大关系的东西,有一些物品......档案或归档的概念与你告诉我的有关,不是吗?
是的,也许更多的是一种精神档案,而不是物质档案,因为从这个角度来看,我的档案相当凌乱;所以,“档案 ”是一个美丽的词,但对我来说,却是非常凌乱的。不过,从某种角度来看,这里也是一个档案馆,也就是说,这里的图像就像档案馆里的图像一样。事实上,我已经存档了成百上千张照片,还有几页几页的文字、著作和笔记,这让我觉得:这已经是存档了,目的是为了做一些事情,总是要做一些事情的。所以这很好,你不知道为什么,但这很好,肯定会有一个时间。实际上,有时这些事情会再次出现,我无法解释为什么,它们都是心理游戏。例如,我曾拍过一块蓝色的布料,显然毫无意义,但一个月后,它突然让我想起了安东内罗-达-墨西拿(Antonello da Messina)的《圣母玛利亚》(Virgin Annunziata),于是我对自己说:’嘿,看,在那片蓝色中,蓝色布料上的褶皱里,有什么东西’。我不认为我在拍摄那块蓝布时想到了安东内罗-达-梅西纳,但他的圣母,那个形象,在我的无意识中很好地呈现了出来,通过与那块可怜的蓝布的镜头进行比较,我找回了它。我不想与安东内罗-达-梅西纳(Antonello da Messina)相提并论,那将是对他杰出艺术的侮辱,但这种与重要事物的联系,我不知道......但它很美。
听着,关于文本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些文本往往具有非常诗意的特点,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唤起了一种抒情的维度。
是的,让我们说,不是描述性的,不是叙事性的,它们必然属于那里。
但不知何故,当你把自己作品的一系列图片放在一起时,观者就会被邀请创作自己的叙事。
啊,当然,个人叙事是的,虽然这不是最重要的,事实上我从未想过。但我知道它之所以会出现,也是因为在看到我一系列包含文字的作品时--并非所有作品都包含文字,但很多作品都包含文字--我们会自动将它们理解为一系列页面,从而将它们作为一系列页面来阅读;一页总是更大的东西的一部分:一本书、一段文字、一本笔记本,等等。因此,我们会寻找这一页与下一页或前一页之间的联系,这些联系实际上并不存在,但同时又是存在的:一切事物都可以以某种方式联系起来,你不这样认为吗?另外,我们可以用音乐的比喻来称呼调性,这是我决定的,也是我的工作方式,因此,就像你所做的事情一样,你会觉得它们都是你的,它们是一个整体的一部分。有时,我觉得自己,当事情已经完成,在决定了哪些作品以及如何安排墙上的作品之后--这是我经常愿意留给其他人的事情,无论是画廊老板还是策展人--在这里,我感知到了一个伪故事,类似于这样的东西,完全出乎意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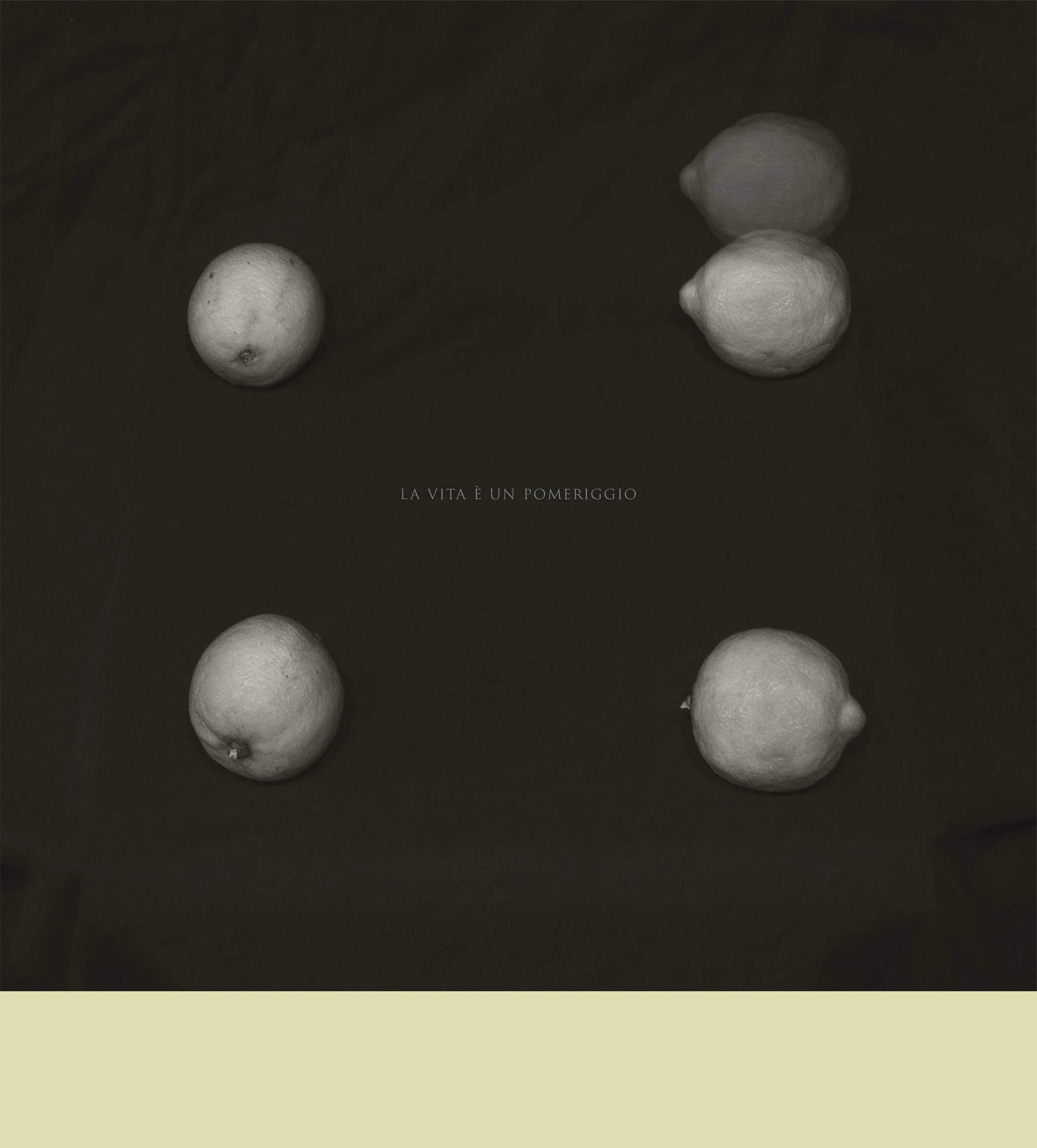





一种氛围?
是的,似乎也有,因为有时文本中的时间人称、语言人称会发生变化,有时是第一人称,有时是第三人称,有时是第一人称复数......。总之,这就形成了一种合唱,一种有多种声音的对话。但这些都是我现在正在思考的问题。
是的,当然,这也是艺术家访谈中最有趣的一点,有时甚至通过谈话就能产生想法。
你自己也是一位艺术家,你很清楚对自己作品的叙述和诠释绝对是最困难的事情,我认为有一部分你必须省略掉。
是的。你不必把所有事情都说出来!
也因为我也不了解我作品的全部;有一部分我不知道,而我认为,矛盾的是,这是我工作中最重要的部分。有时,我无意中听到有人谈论我的作品,并提出了我从未想过的有趣的理由和解释。因此,如果艺术真的能让你思考,它就能让你超越它简单而直观的表现形式。这就像你开始吹口哨、哼歌,然后就会出现大合唱;有些人一开始会和你一起哼,然后你就让它继续,他们就会独自哼出意想不到的旋律,而这些旋律往往比开始的主题更好听。
我还想问你一件事:比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多次使用同一幅图片,或许改变文字,或许只是改变语气或形式?
不完全是同一张图片,也许是同一个主题,这种情况发生过很多次。至于后来是否被用于展览或出版,这就不确定了,但我多年来经常拍摄一些主题。例如,我经常拍摄的一所骑术学校。我跟你说的这些树,我想大约十年前就已经从对面拍过了。要解释原因对我来说很困难,但这就是事实。另外,我跟你说的那块布,我已经在利古里亚的一座教堂里拍过好几次了,我去那里的时候,牧师现在看我的眼神都不好了,因为我去那里,拍的都是中殿最隐蔽的角落,那里实际上什么都没有。
我想说的是,有些情况有利于触发动力,但无法完全解释,它们仍然是神秘的。
这种神秘既体现在思想方面,也体现在创造力和艺术创作方面。当我读到药品骗子们的叙述,或者听艺术家们自己完整地解释他们所做的一切、他们作品背后的计划、他们想说的和不想说的--这种情况在新一代中经常发生,我不知道你是否也遇到过--他们绝对知道他们所做的一切以及他们为什么这么做。我并不钦佩他们,事实上我很恼火。好像有必要进行千篇一律的解释,我还看到,在基层有大量的计划:’你做了这个,我做了那个’。现在,从社会、生态到性别相关的某些领域、某些主题的工作非常时髦;因此,有些作品虽然是条约,但却失去了艺术的神奇和神秘的一面。最重要的是,它们受到了历史的限制,受到了编年史的限制,而编年史赋予了它们存在的理由,使它们即使在质量上平庸也是合理的。我想起了朱利奥-保利尼(Giulio Paolini)说过的一句话(艺术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是淫秽的),我认为艺术必须影响社会,即使这很困难,但艺术本身必须影响社会,而不是相反。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各个层面的文化问题,而在许多(注意,不是所有,但仍然太多)机构及其高层管理中都缺乏这种文化,甚至更加缺乏......我现在将保持沉默。
当然。它不能追着社会和社会问题跑。
它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且,如果有的话,作为思想和推理的触发器进行干预。它的干预必须是一种内在的方法......
是的,正是如此,否则你就会进入所有其他领域,而这些领域与艺术毫无关系。
前段时间,我和一位画廊老板,一位非常睿智的人,聊到这些话题时,我问她:“但听着,我们应该做什么?艺术家能做什么?”她回答说:“他必须继续做一个艺术家,他必须做自己的事情。而这种 ”做自己的事“,在有人观察它、有人反思它,甚至在它发生时进行批判之后。因此,我们又回到了之前的话题。从这里开始,可以产生对社会有益的东西,但这只是因为你在制造、创造动机、思考的原因和反思。艺术必须是自己的东西。它不能借用时事的主题,尽管它是时事的一部分。因为如果我把时事作为一个纯粹的借口,因此远离真正的参与--现在很多人都这样做--那么从历史上看,我就完了,因为再过六个月或六天,时事就已经是另一个时事了。因此,我的工作,我的 ”假参与",将是完全不可理解的,空洞的。相反,安东内罗-达-墨西拿(Antonello da Messina)的《安娜齐亚塔》(Annunziata)将继续讲述这个故事,它的面前永远摆着那本书,而作为观察者的我却不知道它在读什么,也不知道它为什么看着我。这才是我们要做的工作。是的,这就是通过保持当代性,使我们超越日常时间的沉重泥泞的地方。我们必须这样做,做真实的自己,这是我们欠自己的。

本文作者 : Gabriele Landi
Gabriele Landi (Schaerbeek, Belgio, 1971), è un artista che lavora da tempo su una raffinata ricerca che indaga le forme dell'astrazione geometrica, sempre però con richiami alla realtà che lo circonda. Si occupa inoltre di didattica dell'arte moderna e contemporanea. Ha creato un format, Parola d'Artista, attraverso il quale approfondisce, con interviste e focus, il lavoro di suoi colleghi artisti e di critici. Diplomato all'Accademia di Belle Arti di Milano, vive e lavora in provincia di La Spezia.免责声明:本篇意大利语原文的中文翻译由自动工具生成。 我们承诺会对所有文章进行审核,但无法保证完全避免因软件造成的翻译误差。 您可以点击 ITA 按钮查看原文。如发现任何错误,请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