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许多研究都旨在重新解读罗伯托-隆基的历史和批评作品。这表明龙吉已经进入了历史进程的阶段,而这一进程将决定他是否被最终封为圣徒。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在吉安弗兰科-孔蒂尼(Gianfranco Contini)看来,龙吉是 20 世纪意大利最伟大的散文家之一,但在今天的国外,由于他的写作风格使其难以翻译,因此很少有人阅读和了解他(另一位付出同样代价的作家可能是乔瓦尼-特斯托里(Giovanni Testori))。几个月前,埃诺迪在《千年》丛书中出版了龙希的文集,这标志着人们开始关注他的人生道路。这本文集实际上是著名的《Meridiano Mondadori》文集的重印本,该文集于 1973 年出版,在评论家去世三年后由 Gianfranco Contini 编辑(在 安娜-班蒂 的监督下),但增加了两部分内容:彩色照片和由 31 位学者撰写的评论注释,作为文集中每篇文章的导言。奇怪的是,尽管两本书的格式截然不同,但《梅里迪亚诺》和《千禧年》的页数却大致相同(略低于 1200 页)。总编辑由两位相关专家克里斯蒂娜-阿西迪尼(Cristina Acidini)和玛丽亚-克里斯蒂娜-班德拉(Maria Cristina Bandera)担任,她们还撰写了导言,导言中还加入了文本与图像之间关系的主要专家之一琳娜-博尔佐尼(Lina Bolzoni)的介绍性说明。
这个珍贵的版本并没有抹去人们对于将《梅里迪亚诺》中由埃米利奥-切奇、詹弗兰科-孔蒂尼、朱塞佩-德罗贝尔蒂斯和皮埃尔-文森佐-门加尔多撰写的文字总结的整个开头部分从书卷中删去的选择所产生的巨大分歧,这些文字经过调整,旨在强调龙希作为艺术散文作家的写作风格和文学天才。可以说,在这种方法中,对隆基的批评评价不如他作为作家的伟大来得重要,因为他的特立独行也很伟大,在这样一位驯兽师的鞭子下,这些特立独行成为了 “相反 ”的反语直觉。
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要将孔蒂尼的有序选集作为一个整体,甚至将标题 "Da Cimabue a Morandi "也照搬过来,在文本选择上不做丝毫改动,却完全删除而不是更新附录,从而不恰当地盗用有地位的批评家的作品,却又将他们的文章排除在新版之外。为什么不将本卷与其他未收录的著名文章整合在一起,例如将 1952 年关于卡拉瓦乔的文章与 1968 年出版的文章放在一起,突出概念上的差异?或许还可以将1951年展览的导言作为附录,强调从目录初版到展览开幕一个月后的再版之间,龙希对他的导言做了一些 “更正”,基本上都是风格上的更正,这表明即使是伟人也有更正印刷书籍的诱惑,但最重要的是证明文字在龙希的批评工作中是多么重要。因为风格就是这样一种东西:认识到什么是你内心深处的东西,什么是无法改变的,就像你眼睛的颜色或你的指纹一样,并通过阅读现实(在这里是指艺术家、作品和历史发展)来实地证明它。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排除《子午线》的介绍性文字,而不是将其移至临时附录中呢?这就好比我们想走一条与孔蒂尼指示的不同的道路,但又不能否认选集的拼凑,以便更加突出龙吉的批评见解在艺术史学中的分量。然而,龙吉作为一位出色的鉴赏家和批评家,不是从一开始就以展示一种带有诗意和文学色彩的语言为荣,并以此作为解释和表达他与批评对象手拉手关系的特殊手段吗?写作是一种方法,因为与学术界的看法相反,批评是一门知识,而不是一门科学。因此,每一个判断都有其相对性,因为它可以被多年后的同一个批评家证实或改变,甚至推翻他或她自己的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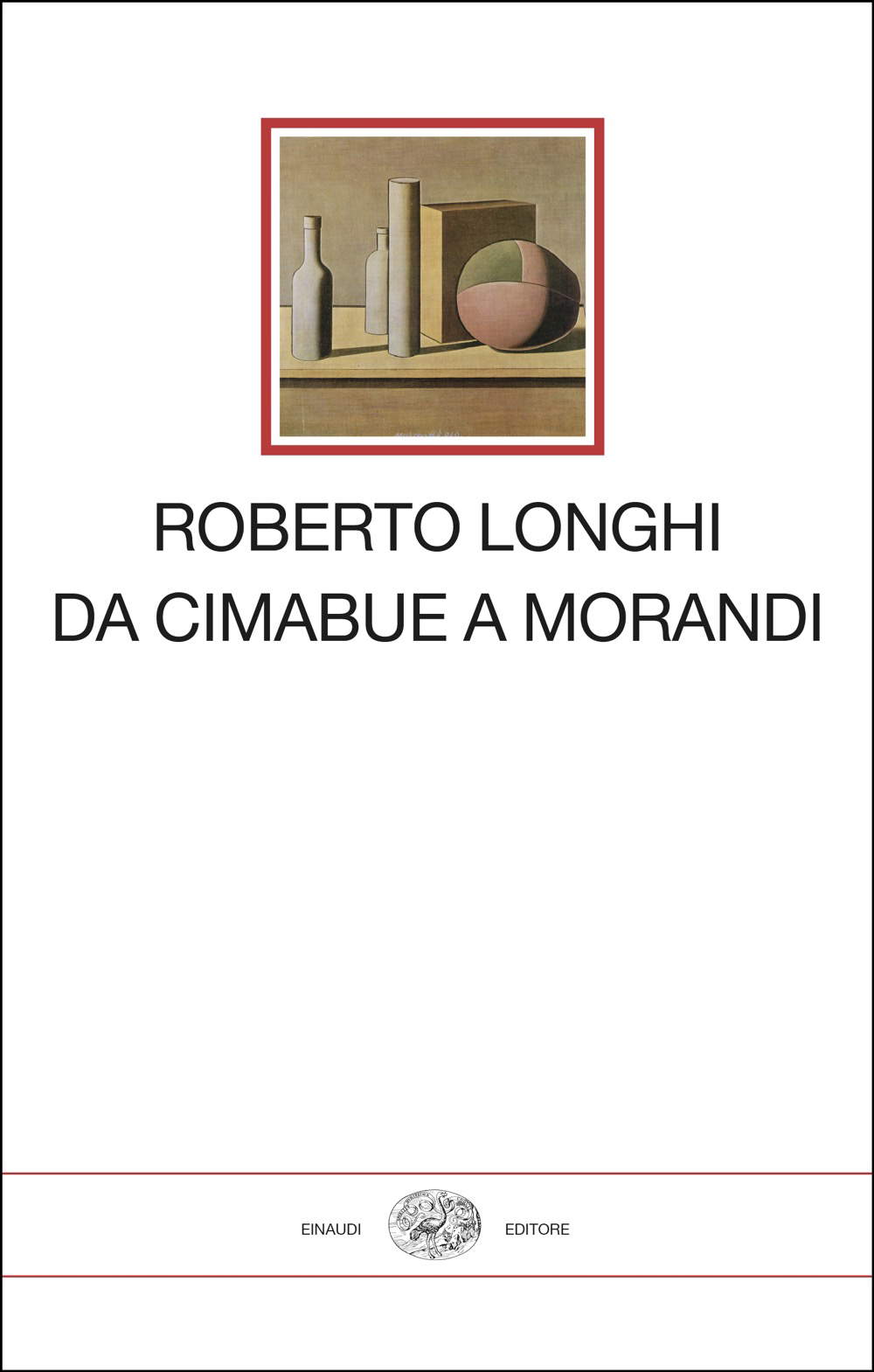
龙希的非凡之处恰恰在于他评论文章的韧性,即使是以夸张的形式表现出来(特斯托里在这条道路上紧随其后,增加了多态作家的音调,与他的大师不同,他处理诗歌、小说、戏剧、政治谩骂,将它们的物质转移到艺术评论中)。通过口头语言(ecphrasis)让作品说话,这是他的一些弟子可能不再认为具有现实意义的选择(今天,知道如何在作品旁边加上一个令人回味的词,而不是沦为技术性或概念性套语的评论家在哪里?我在上一篇关于门德里西奥展览的文章中也提到了这个问题)。无论是策展人或博物馆管理者的硕士学位,还是对数字媒体的习惯性使用所导致的实质上的冷漠,如今许多人都认为批评这一职业不能再不屈服于科学仪器、对图像和材料的各种诊断,以及对作品和艺术家之间的逐步分析分离。龙吉始终捍卫眼睛的首要地位,捍卫鉴赏家的优势:“首先是鉴赏家,然后才是历史学家”。有鉴于此,将龙希的 “典范 ”文本之一,即 1950 年创办《Paragone》杂志的《艺术批评建议》(Proposte per una critica d’arte)作为龙希《千年》的附录,将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可能存在局限性,但在批评文学史上横向显示出的 “重写本 ”仍然是一个值得反思的范例。
龙吉也因此而跻身于文学史;但他将批判性语言视为通过咏叹调进行诗意表达的观点,却没有得到反驳,而法国的亨利-福西永(Henri Focillon)等历史学家和评论家则对这一观点进行了相对化。他以最古典的风格表达了对现代性开放的视野,以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哲学,尤其是 "时间"(ladurée)和 "生命力"(l’élan vital)为出发点,这使他在人文主义之前同样对人类维度持开放态度。持续时间是对时间的主观感知,而生命力则是人类创造力产生的差距,它导致了进化发展。福西永的《手的赞美》作为《形式的生命》(Life of Forms)的续篇,仍然是 20 世纪艺术批评中最富内涵的理论文本之一:法国历史学家在 20 世纪 30 年代重述了他的见解。父亲维克多-福西永(Victor Focillon)并不是一位天才艺术家,但他从小就非常熟练地掌握了包括绘画在内的各种技法。就这一点以及他的历史和评论文章而言,福西永仍然是一位不亚于隆基的重要作家,我在阅读他的文章时总是感到有些困惑,比如托马索-托瓦格里埃里(Tommaso Tovaglieri)在《Saggiatore》上发表的罗伯托-隆基(罗伯托-隆基)的文章《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史学家的神话》的标题。这是一部令人回味无穷的六百页纪录片,从1970年6月3日这位批评家在佛罗伦萨逝世开始,以令人吃惊的 "à rebours "为起点,将龙希一生中交替出现的上百个人物唤上舞台。托瓦格里尼以告别的戏剧性场面揭开了他的 “重写本 ”的序幕,但从根本上复制了神话一开始的绝对状态:龙吉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也就是说,他是一个细节的占卜者,能够帮助他确定作者的身份(这也是龙吉向他的学生们提出的著名 ”谜语 “的实质,要求他们从作品的简单翻页中猜出谁是绘画的作者)。但是,这种 ”颠倒人生年表 “的方法试图将龙希的个人历史与艺术史占卜者的历史结合起来。因此,阿坎吉利和其他评论家在门德里西奥展览上宣扬的口号不可避免地仍然是:”我们不能不称自己为隆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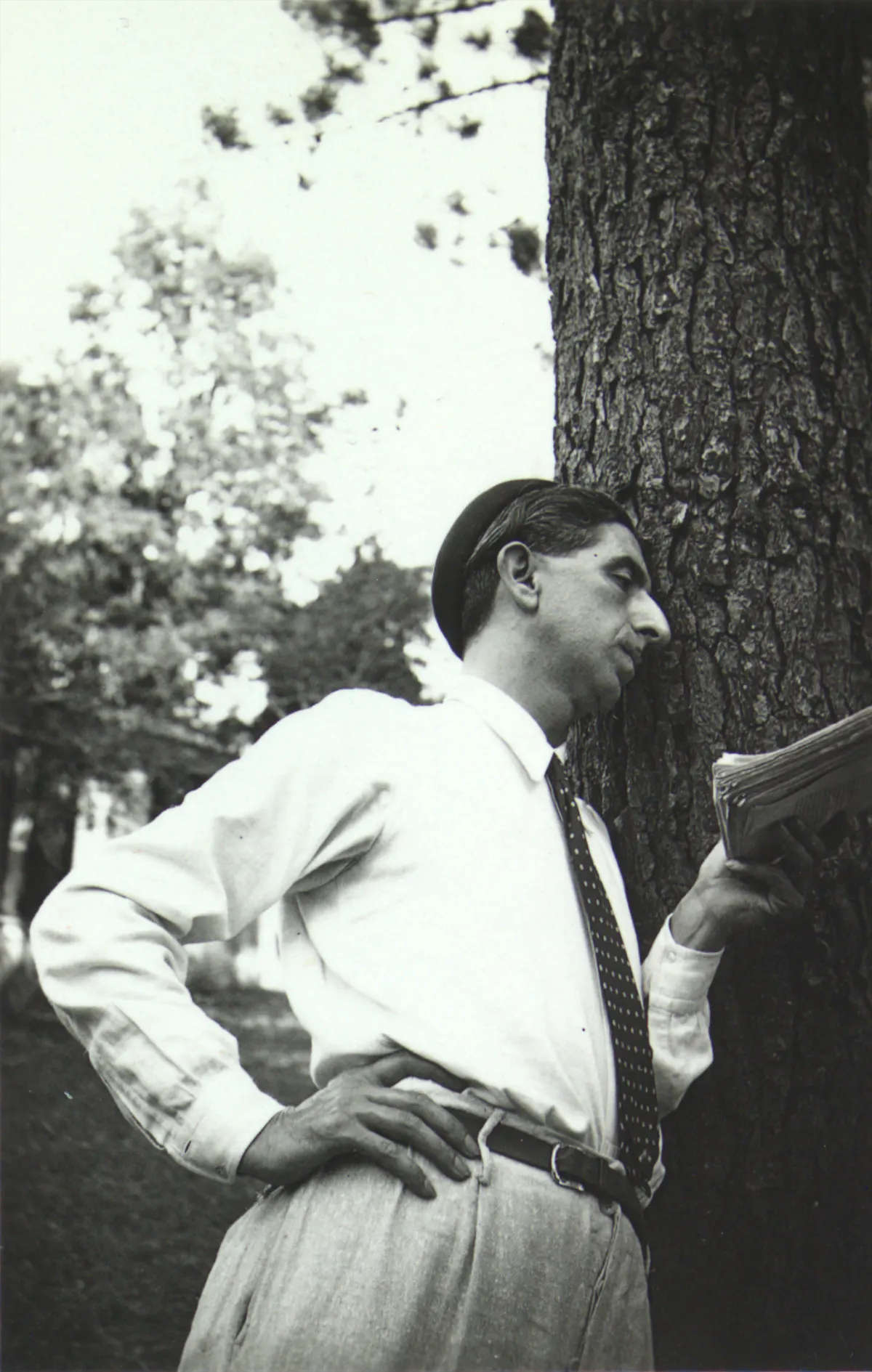

最近,著名卡拉瓦乔学者基思-克里斯蒂安森(Keith Christiansen)在介绍巴贝里尼宫(Palazzo Barberini)举办的回顾展目录时,再次引用了伯纳德-贝伦森(Bernard Berenson)的话,他在关于卡拉瓦乔 “不协调 ”的文章中写道:“大多数学者、哲学家和评论家的诡辩是,他们想从艺术家的艺术特征和品质中找到他的私人生活。因此,克里斯蒂安森补充道:”这篇文章反对将卡拉瓦乔巨大的艺术魅力及其作为画家的成功贬低为仅仅反映其传记中的外部事件"。说卡拉瓦乔在《博尔赫斯歌利亚》中画的是一个绝望而忧郁的人的自画像,是在贬低他吗?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声称--实际上我是这么认为的--委拉斯开兹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画家,因此也是卡拉瓦乔的最伟大的画家,这是否意味着从梅里西的绝对天才身上抹去了什么?可以说,委拉斯开兹是最伟大的画家,但卡拉瓦乔比他更像一位艺术家。也就是说,卡拉瓦乔更有能力将人类转化为绘画形式,但在执行方面可能不够完美。在不完美中发现通往完美之路,这是一句老话。卡拉瓦乔将其贯彻到底,正如詹巴蒂斯塔-马里诺(Giambattista Marino)在《Atlante Nano》中写道:“谁会说其他基督徒/我不是更优雅、更英勇,/如果在我身上连缺陷都变成了优雅,/不完美让我变得完美?卡拉瓦乔当然没有这么讽刺,但问题是:某些不完美,比如他不得不画自己的手,是否会使他的艺术不那么伟大?”但没有证据表明卡拉瓦乔认为他的艺术是表达个性的工具。克里斯蒂安森总结道:“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一位艺术家像伦勃朗那样沉迷于自省,在伦勃朗无与伦比的自画像系列中,我们似乎看到了他作为艺术家和作为人的自我建构的演变过程。克里斯蒂安森总结道:”我让读者自己去判断这些说法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我们对卡拉瓦乔的了解和认识。不过,我想强调的是,提起贝伦森,并声称作品与梅里西的自省不匹配,有一种远离朗格尼安路线的味道,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班提安路线。
在展览目录《卡拉瓦乔与新月》(Caravaggio e il Novecento.罗伯托-隆基和安娜-班蒂的画展将于7月20日在佛罗伦萨的巴迪尼别墅举行,关于安娜-班蒂,福斯塔-加拉维尼写道:"美丽的《Lotto》可以说是一本’隆基式’的书,因为它寻求一种形象化的语言,可以说是用笔再现了画笔的工作。然而,安娜-班蒂的笔则是小说家的笔,如果她表现出对绘画的敏锐阅读,她就会重构艺术家多灾多难的沧桑经历,从而揭示出画家心中的那个人“。小说家意识到,这条道路可能会导致错误,但 ”比起简单地还原事实,小说更能让人接近真相“。如果说贝伦森知道自己伤害了龙希的自尊心,说家族的天才是她安娜-班蒂(安娜-班蒂)和露西娅-洛普雷斯蒂(anagrafe Lucia Lopresti)(埃米利奥-切奇(Emilio Cecchi)本人也以自己的方式认同了这一观点),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遇到未来的妻子后,龙希的语言从他的语言从《Voce》中的抒情表现主义(他也擅长造型创作)向更文学化的形式发展,尽管仍然令人回味无穷,但产生 ”咏叹调"(ecphrasis)的语言摹仿却以谦逊的态度进行,因为他意识到图像和文字之间永远不可能存在同一性,因为它们是两种性质不同、不可调和的成语。
在佛罗伦萨举办的展览由隆基基金会主席克里斯蒂娜-阿西迪尼(Cristina Acidini)和克劳迪奥-保里尼(Claudio Paolini)策划,并附有曼德拉戈拉出版社出版的图录,图录内容丰富,对班蒂进行了多方面的介绍,班蒂是罗伯托作品的忠实守护者,但在隆基去世后,她作为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也体验到了不同的自由。获奖公司 Il Tasso(两位作家的故乡)的杰作是创办了《Paragone》杂志,每期交替刊登艺术和文学作品。自 1950 年以来,《Paragone》杂志月复一月地出版,批评的舞台就在杂志的材料中。毫无疑问,这个想法来自于已经创办并指导过其他艺术杂志的龙吉,但这本期刊的诞生无疑是与安娜-班蒂共同发起的,尽管期刊的封面上写着 “罗伯托-龙吉创办”。恰恰是这种 “内部 ”能力的分离--艺术/文学--反映了一种微妙的对立,与 1951 年卡拉瓦乔画展后朗基最终成为的神话相比,班蒂长期以来受到了惩罚。班蒂被评为 20 世纪意大利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而这一阴影正在逐渐消散。




展览图录是一本由不同作者撰写的书,准确地说应该是20位作者的书,之后是展出作品的登记表,在这本书中几乎处于边缘地位,在登记表的顺序中应该注意到龙吉为他的妻子所画的众多肖像。唯一的缺点是标题,它再次利用了卡拉瓦乔的神话,他的《被蜥蜴咬伤的男孩》(Ragazzo morso da un ramarro,实际上是蜥蜴)被展出来吸引公众。但不应忘记的是,龙希的收藏中还有博尔佳尼、瓦伦丁-德-布洛涅、尤塞佩-德-里贝拉的作品(但龙希不喜欢里贝拉的画,因为他的画分析性太强,正因如此,他不理解斯帕尼奥莱托的手与《所罗门的审判》大师的手是一样的,他认为这幅画出自法国地区,20 年前吉安尼-帕皮(Gianni Papi)的论文对这一事实进行了还原,在里贝拉前往那不勒斯之前,重新考虑了他在罗马的影响力)。莫兰迪显然是此次展览的主宰者(正如龙吉(Longhi)为莫兰迪撰写的文章也是 Meridiano/Millenni 文集的收尾之作),他的作品有 11 件,此外还有卡拉(Carrà)、莫洛蒂(Morlotti)和马卡里(Maccari)的作品。
在近年出版的论文中,有一篇由马尔科-马斯科洛(Marco M. Mascolo)和弗朗切斯科-托奇亚尼(Francesco Torchiani)撰写,名为《罗伯托-隆基:两场战争中的悖论》。Officina libraria 出版的《Percorsi tra le due guerre》或许是让我对过去二十年中出现的某些问题进行反思最多的一篇文章,它让我相信,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节点上,要想提升龙吉,就必须将他 “非神话化”;例如,从他的反叛开始 “回顾龙吉”。这就需要在不否定神话的前提下保持神话。从 “没有绘画”(Keine Malerei)开始--这是一篇写于 1914 年的文章的标题,直到 1995 年才由 Cesare Garboli 出版。在这篇 “特立独行 ”的文章中,龙吉毫不留情地抨击了所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北方艺术。他的语气是神圣的:“...要么这只可憎的羔羊永远不再从倾斜的草坪上滑向喷泉......”(他在宣泄自己的毒腺,表达对凡-艾克和根特神秘羔羊祭坛的厌恶)。Keine Malerei团队还包括丢勒、霍尔拜因、富凯、梅姆林以及其他法国、佛兰德斯和德国画家:“加在一起--什么都没有”,检察官毫不留情地总结道。是什么惹恼了他?他不喜欢北欧写实主义,在他看来,北欧写实主义只是一种技术展示主义,是对现实的模仿,但没有艺术。
马斯科洛和托尔恰尼的这本书非常有用,因为它准时总结了这位伟大评论家的思想起伏:从与克罗齐美学的对比关系--年轻时持保留态度,与理想主义抽象派保持距离,到 20 世纪 40 年代回归克罗齐的立场,从而摆脱了他与博塔伊在部长一级合作的动荡阶段--到他从博洛尼亚大学辞职。1941年,他在佛罗伦萨召开了著名的意大利艺术与德国艺术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年轻时的特立独行(尽管对丢勒持保留意见)在 “区分是为了统一”(非种族主义和非民族主义意义上)这一观点的评价中得到了化解。简而言之,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超越了所有的地方主义。
龙吉从来不是法西斯主义的反对者:1932年,他拿到了党员证,没有党员证,在意大利就很难做任何事;1935年,他宣誓效忠法西斯政权;“官僚主义的例行公事”,这样说来让人不寒而栗,因为他与政治现实的 “妥协 ”即使在1938年种族法通过时也没有倒下,当时他在罗马被博泰拉拢。加博利在谈到 “伴随他一生的综合症,就像他蓝色羊绒夹克上的头皮屑,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 ”或 "LonghiKeine Malerei“时,有效地总结了这一问题:他是 ”先锋派、未来派、理想主义、时事主义、民族主义、反帕萨特主义、声乐家“,他的作品以 ”反复无常、烟雾缭绕、难以翻译的语言,让人惊奇、陶醉、诱惑,只为表达而非交流,只为同胞而作"。
最后,我想提及的是,龙吉毕业后曾在罗马与阿道夫-文图里和《艺术》杂志合作。当时阿比-沃伯格(Aby Warburg)也在罗马,与文图里商讨组织将于1912年在科西尼宫(Palazzo Corsini)举行的第10届国际艺术史大会,会议主题与隆基在1914年提出的主题相同:意大利与外国艺术(主要是北欧艺术)。正是在这里,沃伯格对希法诺亚宫的壁画进行了著名的黄道十二宫解读。当时,一些德国学者认为南欧艺术--正如考古学家朱利叶斯-舒布林(Julius Schübrin)所说--是 “血缘和本能的蛊惑”。最近,汉斯-贝尔廷(Hans Belting)写道,普鲁士政府在那次大会上的期望是在玩一场 “德国与世界其他国家 ”的游戏。龙吉肯定关注了这次讨论,但我不知道他是否会见了沃伯格(当然,关于希法诺亚壁画的报告,无论如何是以寓言和象征的方式进行的,肯定引起了他的注意)。两年后,德国历史学家在他们的报告中表达的北欧优越感,可能助长了Keine Malerei和 Longhi 的骄傲情绪。

本文作者 : Maurizio Cecchetti
Maurizio Cecchetti è nato a Cesena il 13 ottobre 1960. Critico d'arte, scrittore ed editore. Per molti anni è stato critico d'arte del quotidiano "Avvenire". Ora collabora con "Tuttolibri" della "Stampa". Tra i suoi libri si ricordano: Edgar Degas. La vita e l'opera (1998), Le valigie di Ingres (2003), I cerchi delle betulle (2007). Tra i suoi libri recenti: Pedinamenti. Esercizi di critica d'arte (2018), Fuori servizio. Note per la manutenzione di Marcel Duchamp (2019) e Gli anni di Fancello. Una meteora nell'arte italiana tra le due guerre (2023).
免责声明:本篇意大利语原文的中文翻译由自动工具生成。 我们承诺会对所有文章进行审核,但无法保证完全避免因软件造成的翻译误差。 您可以点击 ITA 按钮查看原文。如发现任何错误,请联系我们。